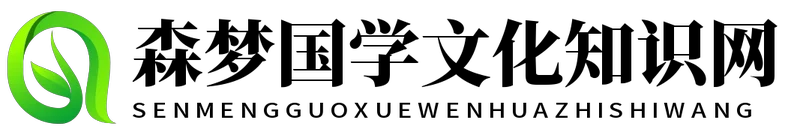摘要:汉语“本体论”与“存在论”应当严格地区别开来,前者对应传统的“ontology”,后者对应的则应当是“Being theory”,因为后者思考的并非形而上的存在者,而是前存在者的存在。尽管前者可以汉译为“存有论”,但后者却不能,因为汉语“有”的本义是一种存在者化的观念,在哲学上所指的正是作为形而上存在者的本体。所谓“汉语哲学”,其中心任务应当是揭示中国哲学关键词的存在论意义。汉字“生”“在”“存”的本义,即人与草木浑然不分的共在,都是中国远古先民对存在的感悟,从而具有存在论意义;而“活”的本义作为“水流声”,则表征着人是由于倾听“天命”而得以存在的,从而具有当代诠释学的意义。 关键词:汉字的本义;生活;存在;本体论;存在论 最近这些年,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一个动向,叫作“汉语哲学”,就是用汉语来讲人类普遍的哲学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讲“汉语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从汉语的角度来讲“存在”(Being)问题。其次,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那么,通过考察这几个关键词的本义,基本上就可以看出,对于全世界哲学所面对的这个核心的“存在”问题,中国人最初是怎么理解的,即这些汉字最初出现、最初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一、汉语“存在论”与“本体论”的概念区分 为了讲清楚这些问题,须先解释“存在论”这个概念。 大家知道,汉语“存在论”这个词语,中国以前是没有的,它是对英文ontology的翻译。但是,英文ontology在近代传入中国以后,通常的汉译不是“存在论”,而是“本体论”。我们今天在汉语哲学文本当中看到的“存在论”和“本体论”其实是一个意思,其所对应的是同一个英文词,即都是ontology。但是,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要讲清楚这个问题,从哪里开始呢?我们从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切入。 海德格尔认为,轴心时代以来,比如说从西方的古希腊时代以来,或者说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都是ontology的问题;但是,这种东西现在已经不行了,过时了。他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叫作《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就是讲传统的ontology,也就是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应当终结了。在他看来,传统的ontology是形而上学,它固然要为各个形而下的学科奠基的;但是,它本身却是需要被奠基的,或者说是有待于奠基的,而这恰恰是传统ontology的盲点。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可以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那么,用什么来为传统的ontology奠基?海德格尔自己发明了一套理论,就是关于“此在”(Dasein)的“生存”(existence)的理论。他把自己的这种理论叫做“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 ontology),也有人翻译为“基础存在论”,意思是说:传统的本体论需要被奠基,用什么来奠基?就应当用这个基础本体论来奠基。为什么?因为传统本体论已经不会思考“存在”,或者说“遗忘了存在”,它所思考的全是“存在者”,是“存在者化”的思维。 所以,海德格尔又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本体论区分”(ontological difference),或者翻译为“存在论区分”,就是严格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在他看来,过去两千年的传统哲学遗忘了存在,它们所思考的全都是存在者:为了说明形而下的众多相对的存在者何以可能,而来构造一个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但是,不论形而下的存在者,还是形而上的存在者,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这就是“遗忘存在”。他提出“本体论区分”或“存在论区分”,就是要“追问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要为存在者奠基,也就是为传统本体论奠基。这是“双重奠基”,即:传统本体论为众多形而下学奠基,而基础本体论则为传统本体论奠基。 这里不展开谈海德格尔思想,只是简单提一下:其实,他自己关于“存在”的前期思想,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他的后期转向。为什么?因为所谓“此在”(Dasein)其实同样是一种“存在者”,而不是“存在”,因此,用“此在的生存”来为形而上学的传统本体论奠基,这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个体性的形而上学。 关于海德格尔的后期转向,我们这里也不必展开谈。笔者想说的是:对于汉语哲学来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麻烦。麻烦在哪里呢?那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两种本体论,即传统的本体论和他自己的基础本体论,都是ontology。但是,在汉语中,把西文的ontology翻译成“存在论”和“本体论”,其含义是截然不同的。 笔者自己的做法是:在汉语里面做一个区分,然后再回过头来在英文里面找到不同的对应: 一方面,凡是谈到传统意义的ontology、思考形而上的存在者的时候,笔者用“本体论”。这本来是中国哲学的概念,它是“形下—形下”的观念架构;不过,西方哲学大概也是一样。中国哲学讲“形下—形下”的架构,有两种说法,即“本—末”的架构和“体—用”的架构。“本”和“体”合起来,就是“本体”,它和西方哲学传统的ontology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相对应,即都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传统本体论对形而上的存在者的思考。所以,在谈到传统意义的哲学本体论的时候,笔者不用“存在论”,而用“本体论”。 而另一方面,凡是谈到为传统ontology奠基的“存在”理论,笔者用“存在论”;而且,其所对应的英文不是“ontology”,而是“theory of Being”或者更简洁的“Being theory”。这其实意味着对海德格尔的“fundamental ontology”的批评。海德格尔想做的事情,是要回到存在本身,重新为传统本体论的存在者化的东西奠基,即用“存在”为“存在者”奠基;但是,他仍然用“ontology”这个概念,这就造成困惑。 这里强调一下:20世纪以来的哲学,和20世纪之前的哲学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其实都是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这个区别就是: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哲学,都是“存在的遗忘”;我们今天的思想或者哲学的真正的“存在论”,首先要追问的是“何谓存在”。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问:存在是什么?因为:存在不是“什么”,即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存在者。当你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你已经预设了答案,就是说,你已经把存在预想成了一种存在者,也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东西”,那就错了。任何可以想到、可以“思议”的东西,都是存在者,中国人叫做“万物”,包括人在内。但是,当我们追问“存在者可以可能”的时候,那就只可能有一个答案:“存在”。存在是什么呢?啥都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是“无”。 以上是笔者为了讲下面几个汉字的存在论意义而先做的一个铺垫。 二、汉字“生”“在”“存”“活”本义的存在论意义 现在围绕本期会讲的主题,讲几个汉字关键词,通过汉语来对“存在”这个哲学前沿的核心观念进行诠释。笔者认为,通过对这几个汉字的本义的诠释,可以把“存在”的观念讲得非常清楚。 (一)“生”的存在论意义 联系“生活儒学”,首先就是“生”字。 我们谈一个汉字的本义,通常绕不过去的就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讲汉字本义的字典,那就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关于汉字的本义,《说文解字》有很多地方谈得很好,但也有些谈得不对的地方,今天的文字学家,特别是古文字学家,包括甲骨学家,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谈汉字的本义,《说文解字》是绕不过去的。 关于“生”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象艸木生出土上。”这就是说,“生”字是由两个字构成的:下面是一个“土”字,上面是一个“屮”字。这个“屮”是一个象形字,就是草木刚刚发芽、刚生出来的那个样子。两个“屮”,就是草木的“艸”字,后来写作“草”。 那么,这和我们这里讨论的“存在”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生”字,我们远古先民在造这个字的时候(甚至在造这个“字”之前,这个“词”已经先出现了),本来是指的草木之生;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最古老的文献《易》《诗》《书》,就已经用这个“生”来说人之生了,指人的生存、生活。例如,《周易》古经说:“观我生进退”、“观我生,君子无咎”。《诗经》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尚书》说:“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我生不有命在天”。 用草木之“生”来说人之“生”,这种语言现象意味着什么?一般纯粹研究语言文字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一种比喻;按其本义,这个“生”字只能用于草木,而不能用到人的身上。但是,我们搞哲学的人,应当对这个问题加以存在论的反思。我们的远古先民,从一开始用这个“生”字的时候,就是既指草木之生,又指人之生。这意味着哲学上的一个重大观念,也就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哲学前沿观念,那就是:这个“生”是一个“前存在者”的观念,即“人”和“草木”这样的区分性的存在者尚未存在,或者说尚未在人们的观念中呈现。这是很有意思的。这种本源情境,《庄子》有一个词语,叫做“浑沌”,即人与神、人与物是浑然不分的。佛教有一个说法,与此类似,叫做“无分别相”;如果你领悟到这一点,这叫“无分别智”。 这种“前存在者”的情境,意味着回到“存在”,这就是“生”字的存在论意义。人们后来的区分性的草木、人,也就是存在者,它们都是由“生”给出来的。这和两千年来的传统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先有一个存在者,然后它怎样去存在。这样的“存在”观念是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前存在者的存在。而“生”的思维方式是反过来的:一切存在者何以可能?都是由存在给出来的。存在是什么?存在不是什么,不是存在者,不是物;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是无。“无”不是“空”,而是最本真的、先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所以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总之,“生”字透露了我们远古先民的“存在”观念,即“无分别”的“混沌”,这才是一切存在者的大本大源。 (二)“在”的存在论意义 按照“生活儒学”的观念,“生活即是存在”。我们来分析“在”字的存在论意义。《说文解字》解释:“在,存也。从土,才声。”这就是说,“在”是由“土”字和“才”字构成的。不过,这里“才声”的说法是错误的,以为其中的“才”只是声符,而不是义符,即没有意义。其实,《说文解字》还有一种解释体例,就是把一个形声字里面的声符同时也看作义符,其表达方式是“从某,某亦声”。按照这种解释体例,应该这样来讲“在”字的结构:“从土,从才,才亦声。”这就是说,某些形声字和它里面的声符,既是同音字,也是同源词;也就是说,这个声符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和这个形声字的整体意义相通的。具体来说,“在”字里面的“才”字不仅是声符,同时也是义符,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是和“在”字的整体意义相通的。 不难发现,这个“在”字和刚才讲的“生”字是很类似的:两个字都从“土”;“在”字里面的“才”和“生”字里面的“屮”也是相通的,都是草木初生的样子。《说文解字》解释:“才,艸木之初也”;“屮,艸木初生也”。 既然“在”字的本义也是草木初生,那么,它跟“生”字一样,如果我们严格地把人与非人的草木区别开来,“在”字就不能用到人身上了,不能说人“在”还是“不在”。但事实上,跟“生”字一样,我们的远古先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在”字来说人在不在。例如,《易经》说:“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诗经》说:“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泛彼柏舟,在彼中河”。《尚书》说:“朕在位七十载”、“有鳏在下,曰虞舜”。 这里的道理,和“生”字是一样的,意味着没有把人和草木区别开来。这也是“浑沌”,也是“无分别智”,也是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意味着草木、人以及万物这样的存在者都是由前存在者的存在“生”出来、然后“在”的。 (三)“存”的存在论意义 再说“存在”的“存”字,那就更有意思了。《说文解字》说:“在,存也。”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存,在也。这叫“互训”。不过,《说文解字》却是这样解释的:“存,恤问也。从子,才声。” 这个解释,我们分两层来分析: 1.人与万物共在。这里,“存”字里面的“才”字,和刚才讲的“在”字里面的“才”字一样,《说文解字》说“才声”是不对的,应当说:“从子,从才,才亦声。”刚才讲了,这里的“才”不仅是声符,而且同时是义符,它和整个“存”字、“在”字的意义是相通的。 再进一步来看,在“存”字里面,“才”是说的草木之初生,而“子”则是说的人之初生,两者直接合成一个汉字。显而易见,“存”字更为直接透露了远古先民的这种存在观念:人与草木、人与万物的浑然不分的“共在”。我们今天总是讲人类和自然应当怎么和谐共处,其实我们的远古先民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人和自然界的万物是分不开的,是一家子。这个观念,在“存”字的字形结构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2.爱即存在。不仅如此,特别有意思的是,“存”字不仅透露了存在就是人与万物浑然共在的观念,而且透露了存在即爱、爱即存在的观念。 许慎对“存”字的解释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存”的意思是“恤问”。这个“恤”,就是抚恤金的“恤”。那么,什么叫“恤问”?《说文解字》解释:“恤,忧也,收也。从心,血声。” 这就是说,所谓“恤问”,就是忧虑地问、忧心忡忡地问。这也就是说,所谓“存”,就是带着忧虑去慰问一个人。这个意思,后来保留在“存问”这个词语里面。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忧虑呢?假如你对一个人漠不关心,你肯定不会为之忧虑,不会去“恤问”之,而会“不闻不问”;反过来说,如果你为一个人忧虑,而“恤问”之,那一定是因为一种关心、关切、关爱。这就是“存”字所蕴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爱即存在,存在即爱。这也正是后来儒家的“仁爱”观念。反之,就是所谓“麻木不仁”。 总之,刚才讲了“存”字的两层存在论意义:第一是人与草木、人与非人的共在;第二是存在即爱、爱即存在。因此,“生活儒学”讲:作为情感,仁爱就是存在,存在就是仁爱;爱即在,不爱即不在。这是笔者特别想传达的儒学的一个最具有本源性的观念,即:仁爱与存在是一回事。 (四)“活”的存在论及诠释学意义 再讲一个生活的“活”字,也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它与“诠释学”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解释:“活,水流声。从水,■[上氏下口]声。”这就是说,“活”字的结构,左边是三点水、也就是“水”字,它是义符,意义是“水流声”;右边是它的声符,是没有意义的,但这不是舌头的“舌”字,它的读音是“聒”,以前不是这个写法,后来楷体化了,才写成这个样子。这就是说,“活”是一个形声字,它的意义体现在“水”字上。许慎给出了一个例子,是《诗经》里面的一句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这里的“活活”即水流声。 问题在于:“水流声”之“活活”怎么就变成了“生活”?这也是中国远古先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种生活感悟:你的生活,你的存活,你的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仿佛听到了某种犹如水流声一般的声音。这种声音,我们的远古先民称之为“命”。什么叫“命”?《说文解字》解释:“命,使也。从口、从令。” 命是一种“口令”,是你听到的某种声音。后来中国哲学的“天命”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显然,“活”字的存在论意义就在于:人之所以能够生活、存在,乃是天命赋予的,即“生之谓性”、“天命之谓性”,这就叫作“死生有命”。 不仅如此,作为天命的“活”与西方的“诠释学”之间具有对应关系。诠释学,即hermeneutics,它的词根是Hermes,也就是希腊神话里的赫尔墨斯,他是宙斯(Zeus)及众神的使者、信使,正如许慎所说的“命,使也”,他将神的消息传达给人间。其实,儒家讲的“圣人”也是同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观念里,与神使赫尔墨斯相对应的是圣人。我们来看“聖”字的结构,从“耳”、从“口”,这就已经表明:圣人有一双耳朵和一张嘴巴,他首先是听到了什么,然后把它讲出来,传达给人间。那么,圣人究竟听到了什么呢?他听到了某种“口令”,听到了“命”,也就是“天命”。圣人听到了“北流活活”的声音,这是生活的声音。不过,按照“活”字的普遍意义,不仅圣人,任何人都能够听到“活活”的天命,由此才能存活、生活、存在。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远古先民在造字和用字的时候,这些汉字已经蕴含着西方哲学直到20世纪才揭示出来的最前沿的存在论观念;而过去两千年的哲学,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确实“遗忘了存在”。我们今天讲“汉语哲学”,就是要将汉字的这种存在论意义发掘出来、揭示出来,把它讲透。 三、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刚才涉及的若干问题,这里再做一些简单的补充说明。 (一)汉语“道”与“诚”的存在论意义 首先是关于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话语或者言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西方和中国都有同样的或类似的传统。笔者以前曾经“客串”写过一篇研究西方哲学的文章《语言的牢笼——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西方哲学》转载,主要是说,从巴门尼德开始,直到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西方哲学一直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存在的、可思考的和可言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现代哲学并不存在所谓“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不过,大家尽管可能都知道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但是未必知道汉语哲学也有类似的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些核心范畴,诸如“道”“诚”“命”等,其实都蕴含着“语言与存在之同一”或“言说与存在之同一”的意味。 比如“道”字。《老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发现,在“道可道”这个表达里面,两个“道”字的意思不同。第一个“道”是说的本体,或者是说的存在。过去通常把它理解为本体、实体,是从名词“道路”引伸而来的。其实“道”的本义并不一定指实体。笔者更愿意采取另外一种理解:从甲骨文来考察,“道”应该是“走路”的意思,标识着存在,是动词,而不是名词。第二个“道”的意思却是“说话”。这也是动词,“说话”和“走路”相应。可见这个“道”字很有意思,表明在非常早的时候,我们的远古先民就有了这样一种观念:所谓“道”,既是走路,也是说话,两者是一回事。这就是他们对“道”的存在论理解。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诚”字。《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这是把“诚”提升到了“天道”的层面上,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但是应当注意,“诚”字是由“言”和“成”组合在一起的。许慎说是“从言,成声”,其实按照刚才讲过的《说文解字》的另外一种体例,也可以说“从言,从成,成亦声”。这就是说,“天道”其实是在言说之中生成的。正因为如此,《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这是将“诚”和刚才所讲的“道”等量齐观。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庸》紧接着还有另外一句话:“不诚无物。”这句话十分重要,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诚”不是“物”,即不是存在者;那么,就只能是前存在者的存在。第二层意思是:一切物,亦即一切存在者,都是由诚生成的。显然,“不诚无物”是说:没有诚,就没有任何物,没有任何存在者;这也就意味着,是诚生成了万物、即一切存在者。所以,《中庸》紧接着又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里的“成己”就是生成主体性的存在者,“成物”则是生成对象性的存在者;这就形成了存在者化的“主—客”观念架构,这个观念架构是一切认识论问题或知识论问题的前提。这也可见《中庸》是一个思想观念很复杂的文本,它具有轴心时代的过渡性,就是从存在论过渡到本体论,其实就是儒家早期哲学从存在论过渡到心性论。这种过渡是从孟子开始的,所以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同时,所谓“诚”就是“说话”,所以“诚”字从“言”,即“言成”——由言而成。但这里并不是说的某个人在说话,而是“天命”及其下贯到人的本真的人性(即“天命之谓性”)的显现。不仅如此,不能把“天命”理解为一个实体化的上帝或者自然界。汉代刘熙的《释名》就很有意思,他解释“天”,是用动词来解释的:“天,显也”。天不是名词性的实体,而是动词性的“显现”;换句话说,天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存在的显现,既是“走路”,即“道”,也是“说话”,即“诚”。 总之,在存在和语言的关系上,中西之间按其实是相通的,虽然双方并不等同,但确实是可以相互融通的。 (二)汉语“有”的存在论意义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用“存在”还是“存有”来翻译“Being”的问题。港台儒家喜欢用“存有”“存有论”的说法。实际上,在汉语哲学中,“存在”这个词语出现得比较早,至迟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包括《五经正义》。例如《礼记》说:“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唐代孔颖达疏:“仁犹存也。君子见上大飨四焉,知礼乐所存在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仁犹存也”和刚才讲过的“存”字的本义意味着“仁爱即是存在”也是一致的。顺便说说,“生活”这个词语出现得更早,《孟子》里面就有了,孟子说:“民非水火不生活。”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存有”这个说法。所以,笔者不赞成用“存有”去翻译“Being”。 不仅如此,从“有”字的本义来看,把“Being”翻译成“存有”也不妥。我们来看看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怎么解释“有”字的,那极其有意思,他说:“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 这个解释太奇特了:“有”就是“不宜有”,也就是“不应当有”。他举的《春秋传》即《左传》的例子“日月有食之”,是说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是不应当有的,因为那是不正常的现象。但是,他之所以引证《左传》的“日月有食之”,是因为他对“有”字的字形有所误解,把其中的一个部分理解为“月”。古文字学家发现,许慎这里讲错了,那不是“月”,而是“肉”。汉字里面,很多从“月”的字,其实是从“肉”,就是画的一块肉,后来由于楷体化的缘故,写成了“月”。同时,许慎所说的“又声”也是不确切的,正如刚才讲过的《说文解字》的一种体例,应当是“从肉,从又,又亦声”。汉字“又”,其实就是画的一只手。因此,“有”字是一个会意字,就是一只手拿着一块肉,象征着“持有”“拥有”某种财富。显然,这是一种“主—客”架构的关系,有一个主体和一个对象;换句话说,“有”显然是一种存在者化的观念。正因为如此,许慎的解释“不宜有”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个命题理解为“‘有’是一种不宜的存在者化的观念”。 进一步说,用“有”来表徵形而上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这也正是《老子》的思想。林安梧教授两次提到《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先把“道”放在一边,我们发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种宇宙论(cosmology)的表达,这个“一”就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者,传统哲学把它叫做“本体”;然后,它给出了“万物”即众多的形而下的存在者。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传统哲学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框架,就是“形上—形下”的框架。但是,《老子》前面还有一句“道生一”,显然,这里的“道”不是“一”,即不是形而上的存在者,那就只能是说的先于存在者的存在。 与此相应,笔者经常引用《老子》的另外一句话:“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天下万物”就是说的众多相对的形而下的存在者。那么,它们是何以可能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有”来的,即“万物生于有”。所以,显而易见,“有”就是“道生一”的“一”,就是形而上的存在者,就是本体。但《老子》又进一步说“有生于无”,这就意味着“无”对应着刚才讲的“道”,它不是“一”,不是本体,不是存在者;这就是说,“无”是说的先于存在者的存在。所谓“无”,刚才讲了,这不是“空”,不是没有,而是说的最本真的存在,而不是某物的存在,反而给出了一切物的存在。由此可见《老子》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所以笔者经常引用。 刚才提到《中庸》的“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也是说的“诚”是作为存在的“无”,并给出主体性的存在者即“成己”和给出对象性的存在者即“成物”。 因此,假如用“存有论”来指称20世纪海德格尔之前的那种传统的本体论,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本体论就是讲的形而上的存在者;但是,如果用“存有论”或者“存有”这个词语来指称我们这里讨论的存在论,那就不对了,就是“不宜有”的了,是应当被解构、被重新奠基的东西。 (三)关于“中国性”的存在论说明 说到“汉语哲学”,当然涉及中国哲学的“中国性”(Chineseness)问题。与这个问题类似,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即关于中医和西医的争论问题,这是如今中国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谈两层意思。第一,在笔者看来,传统的“中医”和今天的“西医”之间的区别,其实并不是中西之别,而是古今之别。这并不等于说凡是古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或者凡是古代的东西就是好的。古代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有两种坏:一种是本来是好的、可用的东西,后来不合时宜了,因为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另一种则是从一开始就很坏,就不是好东西。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觉得适宜的东西,将来的人未必觉得适宜。第二,更重要的是,从存在论的观点看,要避免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避免把既有的东西视为永恒的东西。今天的中医话语或者西医话语,其实都是存在者化的。现在讲“建构中国话语体系”,那么,既然中医的话语已经是既有的、现成的,那又何须去“建构”呢?反之,既然要“建构”,就意味着要重建这些东西,那就必须回到前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而不是把前现代的、古代的或者说存在者化的东西现成地拿过来,以为这就是“中国话语”了。这就是说,具有“中国性”的东西并不等于传统的东西;今天中国人所创造和建构的新的东西,同时也就是具有“中国性”的东西。这是存在论视野,即超越存在者化的思维。 此外,所谓“中国性”,当然还涉及中国式的诠释,即涉及汉语的训诂学问题。刚才讲的《说文解字》对形声字的一种解释体例,即“从某,某亦声”,你不能把它作为普遍判断,好像凡是形声字都可以这样讲,都不再是形声字,那就错了;只能说,有一部分形声字可以这样讲,即它的某个构成部分既是声符也是义符,它和整个被解释的那个汉字之间是同源词。这需要音韵学的知识,特别是古音学的知识。大致来说,如果能够确定两个字之间具有这么一种关系,就基本上可以判定它们是同源词:第一,它们有语音上的关联(这跟文字的字形无关),诸如“一声之转”之类,这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第二,它们有语义上的关联,这是可以考察的。不能说随便一个形声字都是这样的,否则就太泛滥了。 总而言之,真正的存在论是追问“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汉语哲学的存在论就是在汉语的资源中追问“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这里所追问的存在者,首先是作为传统本体论的本体的那种形而上的存在者。这同样适用于宗教哲学。在古代中世纪,徒是不敢追问“上帝何以可能”的;但在今天,教的上帝也是可以追问的。同理,中国古代的“天帝”“天”“理”之类也是可以追问“何以可能”的,因为不论是作为上帝的“天帝”,还是作为本体的“天理”,也都是形而上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论追问”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解构—还原—建构”,回到存在,回到生活,从而重建形而上学。 作者: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