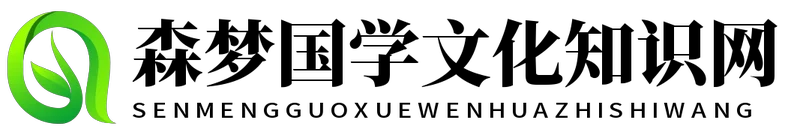摘要:“心外无物”的“物”除指“行为物”之外,还指“存在物”。前者指良知创生的道德践行,意义明确;后者指良知创生的道德存有,争议较多。良知之所以能够创生“存在物”,是因为良知总是以自己的“眼光”审视天地万物,将天地万物笼罩在自己的视野之下,赋予其道德的价值和意义。这方面的内容即为道德存有论。道德存有论是宋代之后儒学逐渐发展出的一条辅线,阳明的努力极大地充实了这一路线,奠定了儒学以道德践行为主、以道德存有为辅的理论格局。将道德存有这条辅线剥离出来,使其不再被夹裹在道德践行主线之内,对于梳理儒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儒家生生伦理学; 道德存有辅线; 王阳明; 心外无物 近年来,我在以儒家生生伦理学重新梳理儒学发展谱系的过程中发现,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内部实际有两条线索,一是道德践行的线索,这是主线;一是道德存有的线索,这是辅线。(1)在道德存有这条辅线中,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儒学形成一主一辅两条线索的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阳明“心外无物”理解的历史与现状 《传习录》中“观岩中花树”的对话是一段争议很大的文字: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07-108 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当时已经有了较大影响,但世人一直难以接受。一次游南镇,友人指着花树向阳明请教,当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如上所引,阳明的回答十分简练,但这种回答仍然无法彻底消除他人的疑惑。 顾应祥是阳明第一代,当时就有这样的疑问: 愚谓花之颜色初不系人之不看而寂也,亦不系于人之看而明白也。孟子辩告子义外之说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盖谓长在外,而长之者在内也。花在外者也,看在我者也。所谓“万物皆备于我”者,谓万物之理皆具于吾心也,若天地万物皆在吾一腔之内,反使学者茫然无下手处矣。[2]388 顾应祥引孟子之语提出质疑。孟子在与告子争辩过程中区分了“长者”和“长之者”,认为长者在外,长之者在内,意即尊敬的对象在外,尊敬的根据在内。岩中花树也当如此看。“花在外者,看在我者”,意即花是客观的对象,在外,看的人是我,在内。不能因我在内而得出花在我之内的结论,否则人们便茫然无下手处了。 有人进而批评阳明这样讲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清儒罗泽南即是如此,他说: 岩谷之花自开自落,不以无人看而寂然,不以有人看而感通。阳明谓未看花时,花与人心同归于寂,至看花时,花色便明白起来。果何从见其明白乎?……盖阳明之学本之释氏,其以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岩花开落与心无关,则花在心外矣,不得不曲言花色一时明白也。[3]487 岩中花树自开自落,即使没有人也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由此证明心外无物。阳明说未看花时,花与人心同归于寂,来看花时,花色便明白起来,这分明是受到了释氏的影响。《楞严经》讲山河大地都是妙明真心中物,即是此意。阳明没有分辨儒学与佛学,造成了混乱。 这种批评一直延续到近代。钱穆认为,阳明“心之感应谓物”,“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等说法,直接将心之感应称为物,明显不妥。钱穆指出: 而有时阳明又曰:“心外无物。”此则又说之更极端,与前说迥殊,而语病更大。《传习录》,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有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此处竟俨如释氏所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尽妙明心中物矣。此与孟子之言良知又何关。[4]140 阳明常讲,“心之感应谓物”,“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这些都有问题。以岩中花树证明“心外无物”,更是极端,语病甚大。这种说法与释氏所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尽是妙明心中之物,已经没有区别了。不仅如此,钱穆对阳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的说法也不满意,明言“此条陈义甚肤,乃似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唯心论,亦可谓是一种常识的世俗之见的唯心论,此正阳明所讥评从躯壳起念也”[4]142-143。这是说,阳明这些说法明显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唯心论,或世俗之见的唯心论,孟子、象山决不会有这种说法。 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学者认为阳明此种观点几无学理意义可言。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在引用阳明观岩中花树一段材料后这样写道: 这是背离事实的捏造。我们知道,感觉只是客观存在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结果,例如“一定长度和一定速度的光波运动,它们作用在眼网膜上,就在人里面引起这种或那种颜色的感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页四十)。然而王阳明却从感觉出发,把人的主观感觉“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页三六五)。[5]884 从唯物主义立场来批评阳明是唯心主义,是那个年代的主基调。 近些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陈来于1991年撰写的《有无之境》对阳明相关思想予以了新的解释: 这个被赋予了高、深诸性质的世界显然不是指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价值的、审美的、具有意义的世界,“他的天地万物”就是他经验范围内形成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离开了他的意识就不成其为他的世界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对海德格尔、萨特、庞蒂都有直接影响,阳明的思想也许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才是可以被理解的。[6]60 在胡塞尔那里,世界是一个现相的存在,这种现相是由人的意识赋予的。没有人的意识,这个现相世界不会存在。阳明所说正是这个意思。在阳明看来,良知是世界的本源,没有这个良知,谁去仰天的高,谁去俯地的深,谁去辨鬼神的吉凶。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地万物都离不开人心,这就叫“心外无物”。学界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2) 但略有遗憾的是,陈来对“有无之境”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似乎偏于狭窄了。他是这样说的: 在本书及以下讨论的宋明儒学的“有我之境”是指“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大“吾”之境,而“无我之境”即自上章以来我们已反复强调的“情顺万物而无情”的无滞之境。[6]235-236 按照这一界定,“有无之境”分别包括“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指受道德之心影响之境,也就是“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大“吾”之境;“无我之境”是指没有造作、没有执着之境,也就是“情顺万物而无情”的无滞之境。依照我的理解,这种区分可能有两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对“有我之境”而言,陈来虽然有详细的分析,但没有特别关注牟宗三的成果,更没有使用“存有”这一术语,而是称之为“境界”。(3)这种做法对学界有很大影响。(4)其次,就“无我之境”而言,陈来正确地指出了无滞是无,但没有讲到未受道德之心影响的万物也是一种无,一种更为重要的无。 二、“物”的两种不同所指:“行为物”与“存在物” 因为儒家生生伦理学是顺着“十力学派”的道路走的,所以特别重视牟宗三的思想。牟宗三对阳明“心外无物”思想有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道德践行的角度,这方面的“物”牟宗三称为“行为物”: 因此,意念之动显然是落在感性的经验层上的。意念在感性的经验层上的活动,因涉及外物,必有其内容。此内容即是阳明所谓“意之所在或所用为物”也。如意在于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此物是意念的内容,因此,我们名之曰“行为物”,亦即所谓“事”也。就“意之所在”说物,那物就是事。[7]453 道德之心的根本任务是创生践行,其发用必须通过意念进行,意念落实在经验层面上,必涉及外物。这种“物”其实就是“事”。“事”即“物”,“物”即“事”,二者没有原则之别。这种由道德之心创生的践行就是“行为物”。 二是道德存有的角度,这方面的“物”牟宗三称为“存在物”: 在感性层之念上带进正不正之“行为物”;在“行为物”中带进天地万物之“存在物”。对此存在物,既须认知地知之,又须存有论地成之;前者吸摄朱子之“道问学”,后者仍归直贯系统之创生,如前《王学章》之所说。如此,门庭始广大。若如蕺山诚意慎独之太紧与太狭,则念无交待,而天地万物亦进不来,心谱即不全。[8]394 在牟宗三看来,在感性层次上讲念涉及道德行为,故为“行为物”。但如果仅有这一层的话,“天地万物”还没有交代,理论还不完整。理想的情况是,既有道德践行之“行为物”,又有天地万物之“存在物”。这里的“存在物”是一个重要提法,所指对象是“天地万物”。牟宗三有时又形象地将这种“天地万物”称为“山河大地”[9]305“一草一木”[10]246。“天地万物”“山河大地”“一草一木”这些不同说法,所指不再是道德践行,而是自然界的外部对象。与此相关的物即为“存在物”,而这种“存在”也就是“存有”。 为了阐明这个道理,牟宗三将良知概念分为主观、客观、绝对三义。“主观义是独知知是知非这一活动”。“客观义要通过‘心即理’来了解。良知之活动同时是心,同时亦是道德的理。若非如此,道德的理便成外在。阳明说良知本身即天理,同时是活动,同时即是理。良知所知之理,即是它自己所决定的,不是外在的。一说到理,良知便是客观的、普遍的及必然的,这才可成为客观义。”绝对义的情况较为特殊。“良知并非只此二义而已。此二者只开道德界,而良知还有一个绝对义(存有论的意义、形而上的意义)。前二义开道德界,这一义开‘存有界’”[11]213。在这三义中,主观义和客观义涉及的是道德践行问题,即所谓“行为物”,“绝对义”涉及的则是存有问题,即所谓“存在物”。(5) 在说明“存在物”的过程中,牟宗三特别重视良知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他这样写道: 良知感应无外,必与天地万物全体相感应。此即函着良知之绝对普遍性。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即佛家所谓圆教。必如此,方能。由此,良知不但是道德实践之根据,而且亦是一切存在之存有论的根据。由此,良知亦有其形而上的实体之意义。在此,吾人说“道德的形上学”。这不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客观分解的以及观解的形上学,乃是实践的形上学,亦可曰圆教下的实践形上学。因为阳明由“明觉之感应”说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曰物”,见上)。道德实践中良知感应所及之物与存有论的存在之物两者之间并无距离。[8]184 良知既是道德的根据,又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根据,由前者可以成就道德践行,此为“行为物”,由后者可以创生道德存有,此为“存在物”。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即道德践行与道德存有,“行为物”与“存在物”其实是一。将这两个方面打通,就是牟宗三着力建构的“道德的形上学”。如果不从道德意义上立论,也可以讲出一套存有论,但那是西方的做法。儒家讲存有论必须从道德的进路入手。按照这种进路,良知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其极无外。这样一来,牟宗三就将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上升到道德存有论的高度,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由此出发,牟宗三进一步讲到了“无”的问题: 良知灵明是实现原理,亦如老子所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云云。一切存在皆在灵明中存在。离却我的灵明(不但是我的,亦是你的、他的,总之,乃是整个的,这只是一个超越而普遍的灵明),一切皆归于无。你说天地万物千古见在,这是你站在知性的立场上说,而知性不是这个灵明。[8]187 从现相学的角度看,意识有其意向性,总要指向对象。在这种意向体验中,意识与对象之物发生了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对象之物。如果没有意向体验,对象不成其为对象,这种意义的“对象”其实也就是“无”。牟宗三准确把握住了这个道理,特别强调良知灵明是一个创生主体,天地万物皆在其涵盖之下。没有了这个灵明,天地万物便等于“无”,即“一切皆归于无”。这里所说的“无”是道德意义的,不是物理意义的,更不是单纯的无滞无执,而是指没有了良知的灵明,天地万物便不会有道德的价值和意义。(6) 要之,不仅重视道德践行问题,而且重视道德存有问题;不仅讲“行为物”,而且讲“存在物”;不仅讲无滞之“无”,而且讲没有良知灵明影响的天地万物之“无”。这是牟宗三关于阳明研究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三、“存在物”与儒家道德存有论 要准确把握牟宗三的上述思想,了解“心外无物”中“存在物”的具体意义,需要对本体、本根、存有这三个概念作出区分。中国哲学所用本体一词与西方哲学不同,主要为本根义。这种本根有两个方面的发用,既有道德践行的发用,又有道德存有的发用。与前者相应的对象叫“道德践行”,与后者相应的对象叫“道德存有”。牟宗三虽然对“存在”和“存有”这两个概念做过区分,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概念是混用的。(7)因此,与“存在物”对应的理论可以说就是道德存有论。 有了这个视角,“存在物”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传习录》中阳明关于“存在物”的论述,除上引“观岩中花树”的例子外,还有三处较重要的文字。 一是“天地鬼神之灵明”: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 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曰:“人又什么教做心?” 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1]124 阳明如此说,从哲学层面解释,其实是要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天地鬼神的意义是我的灵明赋予的。 二是“草木瓦石之良知”: 朱本思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1]107 有人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照这种说法,草木瓦石是不是也有良知呢?阳明的答复令人吃惊: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这种说法从字面看很难理解,因为良知只能对人而言,不能对草木瓦石而言。阳明此处却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此为何意?阳明下面的做了解答。他说,天地万物原为一体,彼此相通。这种,根据上面的分析,只能理解为因为人有良知,以良知的眼光看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便有了意义,从这个视角看,人与天地万物也就和合为一了。由此不难明白,万物合为一体,关键在于人有良知,以此良知观看草木瓦石,草木瓦石也就有了意义。 三是“去花间草”: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12]29 一开始薛侃问,社会当中为什么善难培,恶难去。阳明答道,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培,没有去而已。过了一会又说,这种善恶如果从躯壳上起念,就会有误。接下来的话就有意思了。阳明说,天地之间的花草原本没有善恶,人来观花,便以花为善,草为恶;反之,如果用草,草就为善,花就为恶了。阳明这一说法表明,世间的花与草原本没有善恶之分,没有道德的意义,人之所以以花为善,以草为恶,有了善恶之分,皆由人心对其赋予内容所致。 道德之心可以影响天地万物的存在,有深厚的学理基础。我们知道,牟宗三受教于熊十力,一个重要的转机是听其讲“当下呈现”。呈现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一是道德之心在道德境遇下,会主动表现自己,向人发布命令,告知应当如何去做,从而创生道德的践行。二是道德之心遇到外部对象,会主动表现自己,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外部对象,从而创生道德的存有。这两个方面中,前者已十分困难,后者更为难解。为了阐明这个道理,牟宗三创造了一系列形象的说法,如创生、实现、妙运、神化等等(8)。其意无非是说,道德之心有一种功能,可以使原本干枯无血色的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具有道德的价值。原本没有道德价值,由于道德之心的赋予,变得有了价值,这个过程就叫创生,就叫实现,就叫妙运,就是神化,其结果就是创生道德的存有。儒家的这种理论与西方的存有论有同有异。存有论(ontology)原是古希腊形成的一门关于“存有(在)之为存有(在)”(being as being)的学问。这个存有(being),在巴门尼德那里是“estin”(to be),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to on”,二者来自同一个词根“es”(eimi)。“存有”概念最终诉诸“es”这个在西方语言系统中不能再还原的“起源”(arche),标志着西方存有论对语言的直接依赖。因此,西方的存有论主要是认识论意义的。儒家哲学也有类似的理论,但与西方不同,儒家相关的思想以道德为基础,这方面的理论即为道德存有论,一种不同于西方认知存有论的存有论。 为了帮助加深理解,明白个中道理,我在《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中以中国人何以喜欢梅兰竹菊为例作了说明。[13]314-315我这样做旨在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即道德之心除了指导道德践行外,总要对外部对象表达自己的态度,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其上,创生道德存有。梅兰竹菊原本没有任何道德性,但在道德之心的视域下,也会染上道德的色彩,成为道德的存在。这是中国人将梅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喜欢程度远在其他花卉之上的重要原因。推而广之,因为人有道德之心,道德之心自不容已,一定要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影响外部对象。这种被道德之心影响的外部对象,即为道德存有,而相关的理论,即为道德存有论。牟宗三接续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大讲道德之心不仅可以创生道德践行,由此而有“行为物”,而且可以创生道德存有,由此而有“存在物”,存有论由此成为其思想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牟宗三一生都在为阐明这方面的道理而努力。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也才能把握阳明“心外无物”的哲学意义。(9) 四、从“存在物”看儒家主辅两条线索的整体格局 虽然儒家也有自己的存有论,相关的思想很早就有,但在先秦时期并未成形,一些论述,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中庸》的“不诚无物”,表面看好像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与存有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10)只有随着佛教的传入,到宋代之后,这个问题才渐渐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就宋代儒学而言,很多人都有出入佛门的经历,对佛学万法惟心的思想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受其影响,宋代儒家也开始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关的论述渐渐多了起来。横渠“为天地立心”的“大其心”思想,明显已经包含了这一用意。二程的作用更大。二程能够成为宋明儒学的实际创立者,不仅在于其创立了天理的新范式,为道德践行的路线确定了形上根据,也在于其对道德存有问题多有阐发。明道所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读通读顺。其后,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更是将这个道理讲得简明而直接。阳明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在这方面也迈出了重要一步,而其标志就是“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 由此说来,儒学自创立之始就有一条道德践行的路线,后来受佛教影响,从宋始又辟出了一条道德存有的路线。这两条线索中,道德践行路线为主,道德存有路线为辅,主线引出辅线,辅线助力主线,共同构成儒学发展的整体格局。虽然这项工作直到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才正式完成,但阳明的历史作用绝对不容轻视。阳明“心外无物”不仅包括“行为物”,同时也包括“存在物”,在这方面阳明的确有大贡献。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从理论本身看,这个问题也不容有丝毫的轻视。这条辅线涉及很多极有深度的理论问题。比如,为什么道德之心可以创生天地万物的存有?道德之心创生的天地万物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这种创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牟宗三为什么将这种思维方式叫作“智的直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11)为什么说受到道德之心影响的天地万物是有,而未受这种影响的天地万物是无,而这种无不能完全用无滞无执来代替?这种存有与西方的本体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深入发掘相关义理是彰显儒家学说特色的重要渠道?道德存有对于道德践行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说澄清这个关系有助于颠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传统看这些问题都极具意味,代表着很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其意义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了。尽管“心外无物”在阳明那里主要指道德践行问题(“行为物”),但它同时也包含道德之心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问题(“存在物”)。道德之心总要对天地万物表明自己的态度,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其上,不仅岩中花树如此,一切自然界外部对象都是如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心外无物”这一重要命题才能得到透彻的说明。因此,将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作出具体分析,将其中一部分内容直接标之为“存有论”,上升到“道德存有论”的高度,不再只是以无滞无执讲“无”,也在道德存有论意义上讲“无”,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果真如此,儒家道德践行之主线与道德存有之辅线的整体格局便可以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对儒学两千年发展的整体脉络也就有了全新的理解。(1) 参考文献 [1]传习录:下//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说良知四句教与三教合一//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8]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9]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10]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0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11]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12]传习录:上//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注释 (1)儒家生生伦理学是我在相继结束孟子研究和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后集中精力做的一个项目,相关成果主要见于《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和《儒学谱系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前者是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原理,后者是用建构好的原理重新梳理儒学发展的脉络。在梳理儒学脉络过程中,我有一个重要收获,即发现儒学发展内部其实有两条线索,一是道德践行之主线,二是道德存有之辅线。道德践行问题学界相关成果极多,道德存有问题则关注较少,说法也不统一,亟待加强研究。我之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道德存有路线的展开——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明道历史贡献的新判定》(《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亦与此有关。 (2)杨国荣指出:“在王阳明那里,具有普遍性与个体性之双重规定的心体(良知),同时又是万物的本体。”“理即是万物之所以然者,既然心(良知)与理为一,则由此即可逻辑地导出万物依存于心(良知)的结论。”(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吴震也充分看到了王阳明这一思想的意义,指出:“按照阳明的前提设定,这个世界有两种基本状态:一是‘寂然不动’,一是‘感而遂通’。前者是原初世界,处在一片混沌寂静的状态中,当然这样的世界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或价值可言;后者则是现实世界,人类与其他一切存在构成一整体性、关联性的存在结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存在而不是那样存在的道理、意义以及价值就对我们人类展示了出来。”“深山中的花树到底是什么颜色、如何美丽,如果离开了人,那么,我们就无从了解这颗花树的颜色和美丽,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颗花树作为客体而不存在,而是意味着这颗花树的意义尚未对我们人类敞开。”(吴震解读:《传习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440—441页) (3)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对于有我之境的讨论,主要是在第三章“心与物”中展开的。这一章中分别讨论了“心与意”“意与事”“心与物”“心物同体”等问题,有重要学理价值,但没有充分关注牟宗三的研究成果,也没有明确使用“存有”的概念,未能将相关问题上升到“存有论”的高度。 (4)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一文对阳明相关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文章指出,要理解阳明“心外无物”这一命题,必须由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他的答案不是针对花树是否能离开心而存在,而是赋予‘心外无物’新的含义。即被观看与不被观看的物,对人而言意义不同,把存在论变成意义论问题。”“简言之,‘心外无物’中的关键字不是‘物’,而是‘无’。这个‘无’不是不存在,而是缺乏意义的存在。换句话说,未被心所观照的物,其意义没有在意识中呈现出来。”(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72、76页)按照我的理解,该文看到了意义对于物之存在的重要性,这与陈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他更强调了“意义建构”的重要。这里讲的“意义建构”涉及的其实就是存有论,但他并没有直接使用“存有论”这一术语(该文所说的“存在论”与我说的“存有论”不是同一个概念)。杨立华说:“我们知道他著名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西铭》我一般不讲,我写张载哲学那本书对《西铭》一句都没有提到,我不大喜欢讲境界,山脚下的人说不得山顶上的事,还是朴实一点。”(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这里所说“我写张载哲学那本书”即指《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其中确实没有谈到存有的问题。 (5)无独有偶,耿宁同样认为阳明的良知有三义,只是具体说法不同。在他看来,在1519年之前,阳明的良知主要指一种向善的秉性、向善的倾向以及与之相应的自发的动力。这为良知的第一概念。1520年之后,阳明的良知概念获得了新的含义,同时也指对“我”的所有意念之善恶的知识,即对意念的道德品格之意识,良知即是自身意识,这为良知的第二概念。到了晚年,阳明更加强调良知是本体,这个本体始终是清澈的、显明的、的、不生、不灭,是所有意向作用的起源,也是作为心的作用对象之总和的世界之起源。这为良知的第三概念。这种区分中,良知的第一概念和良知的第二概念指道德践行的内容,良知的第三概念则明显指道德存有的意义。参见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5—381页。 (6)由此说来,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无,一是无滞的无,一是未受道德之心影响的无。以“情顺万物而无情”讲无,是前一种无。除此之外,未受道德之心影响的天地万物也是一种无。换言之,受到道德之心影响的对象为有,未受道德之心影响的对象为无。这种无与无滞之无所指不同,属于两种不同的性质,不能为无滞之无所涵盖。 (7)详见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该书第五卷附录一“牟宗三儒学思想辞典”“存有”条,第270—271页。 (8)我曾将牟宗三相关的说法总结为十二种,即呈现、朗照、润泽、觉润、痛痒、妙运、神化、创生、生化、成全、实现、价值。参见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第三章第二节“存有论的思想核心及其意义”(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7—71页)。 (9)我多次讲过,从儒学发展的总体格局看,存有论才是牟宗三思想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其思想最难把握的部分。非常可惜,学界不少人对此尚无清醒的认识,从事牟宗三思想研究,大多只关注其坎陷论、三系论。这些内容(特别是三系论)当然有意义,但其重要性是远远不能与存有论相比拟的。 (10)这个问题我在《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三卷中有详细分析,请参见该书第94—112页。 (11)参见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三卷第五章“无执存有论商榷之一:关于智的直觉”。 (1)这方面有一个实际的例子。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第六章“‘心外无物’论:‘岩中花树’章新解”充分肯定了牟宗三所说的“存在物”,但又有所保留。他说:“本章对‘心外无物’之诠释始终扣紧在牟先生所说的‘行为物’这一向度上,而对‘行为物’语义之疏通亦未越出牟先生之矩矱。本章所谓‘新解’之‘新’在于,‘岩中花树’章亦可在‘行为物’上得到疏通。且从‘行为物’诠释‘岩中花树’章更能彰显‘心’与‘物’关联之境域生成的‘现场’性质,让‘心外无物’之论说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工夫践履色彩,‘物’即是在道德实践生存境域之中不断构成的。”(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00页)意思是说,牟宗三讲的“存在物”是对的,但陈立胜强调应该将这种“存在物”置于工夫论的视域下。儒学是一门践行性很强的学说,一切都不能离开道德践行这个根基。虽然随着阳明思想的不断丰富,增添了“存在物”这一内容,但不宜将其看得太重。陈立胜的看法自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存在物”的基础仍然是道德,离不开这个根基,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同的领域,包含着极深的意义,将其完全置于工夫论视域下,不仅容易掩盖相关思想的理论价值,而且不利于把握儒学发展的整体脉络。 作者:杨泽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船山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