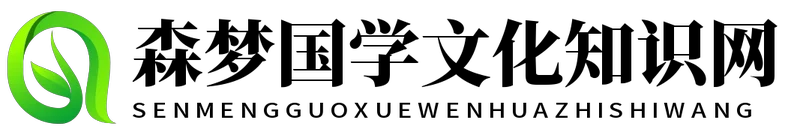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荀子》一书引《诗经·大雅·抑》之篇六次,其中引用“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更是多达三次,分别在《不苟》《非十二子》《君道》三篇。此引诗三处,虽然并无统论之意,但纵览此三篇所引之处行文,其立意逐渐拔高,在“维德之基”的基调下对君子品性展开讨论,最后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见于《诗经·大雅·抑》:“荏染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 郑笺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则被之弦以为弓。宽柔之人温温然,则能为德之基止。言内有其性,乃可以有为德也。”“荏染柔木,言缗之丝”在此章中起比兴兼备的作用,“荏染柔木”之所以是良好材料,正是因为它可用以制作琴瑟乐器,而君子之所以温温然、恭谨守礼是因为其深厚品德作为其根基,故“维德之基”乃是人的内在本质,“温温恭人”是这一本质的外化表现。在《荀子》的语境下,对德为人之安身立命的基础更为强调。在他看来,君子要做到谨慎谦和,持事以敬,不为物欲所倾倒;在位者要做到善政任贤修己而后安政。此二者皆需要坚定的道德基础。 君子应以德为本,行中庸、致至文 《不苟》篇中“夫是之谓至文”是对前文的总结,“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是对“至文”的总结,显然“至文”与“维德之基”并非同一维度的概念,据前言可将“至文”视为“维德之基”的结果。也就是说“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些品质皆需要内在德性的支撑,而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些,在荀子看来已是“至文”。“至文”之境其实无它,凡事把握好度便是其关键所在。因为宽容太过就成了懈怠;太过有棱角则易伤人伤己,“廉”形容一个人有棱角有个性,“刿”为刃伤之意;同样,太过于善辩则易起争执,虽然在荀子看来“君子必辩”,但君子之辩是为了致实,而且君子博学雅正,故其辩能服众不至于发展为争执,君子之辩当如荀子在《非相》篇中说的那样:“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而且,一个人太过于明察就变成了斤斤计较,如此便易激切,现实生活中,太过明察之人往往难以包容他人的短处,自然难以实现和谐,所以杨倞注“察而不激”为“但明察而不激切”;不仅如此,太过于正直之人则不免盛气凌人;太过于刚强则不免凶暴,太过于宽柔则不免随波逐流;太过于恭谨谨慎则容易举棋不定、畏手畏脚。所以把握为人处世的度,是通往“至文”之境的核心要义,而对“度”的把握正是对中庸之道的践行,正如《中庸》所言:“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之所以是舜,就是因为他在面对事物之时用了最合理的适中办法。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进一步理解荀子在此表达的逻辑,那就是以德为基,方能行中庸之道,行中庸之道方能至“至文”之境。如此一来,在荀子这里《大雅·抑》的“维德之基”之德可视为“中庸之道”的基础,德道相通则“至文”矣。 君子应知命自省 如果说《不苟》篇引“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是为了强调君子需以德傍身才能不偏不倚行中庸之道,达到“至文”的境界,那么《非十二子》篇引《抑》则是为了提醒后世儒者“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修身过程中需以“维德之基”自省。荀子以“能”与“不能”为例,指出君子应在主观能动性上下功夫,而不要执着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从自身道德、诚信、才能上督促自我成长,“‘可贵’谓道德也;‘可用’谓才能也”。这些都是个体在充分调动自我能动性的前提下所能实现的,但不能保证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一定会为他人所认可或在客观世界取得成功,但即便如此,真正的君子仍然会以突破自我为目标而努力,如《劝学》篇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家“天命观”认为,客观外在世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即使再执着于某事仍旧有失败的风险,因为客观世界充斥着各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偶然性,而此“偶然性”恰恰是其必然性的体现,故君子应安然接受其必然性,与偶然性、不确定性和谐相处,儒家所倡导的“知命”即如此,知命之不可知,也就无谓成功与失败。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行与不行属于未来偶然性的结果,不应影响当下的自我。所以荀子在谈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这一必然性与偶然性之时,会警示道“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这与孔子所说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君子在内修其身以及立身行道的过程中仍需有一参照,这个参照就是“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这两句诗展现的逻辑关系,正是君子自省的关键。 执政者应“有觉德行”、任贤用能 《君道》引《抑》段落,开头四字“至道大形”,王先谦注此为“言至道至于大形之时”。而此四字即是该段落之主旨,后续行文皆可视为荀子对至道至于大形之时的一种描述,然而这种描述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在天子隆礼至法,尚贤使能的治国之道下国家的应然有序状态。在段落之末,荀子引用“温温恭人,维德之基”,一来,将话题的重点重新拉回到天子身上,言明至道之行关键在于君道,而君道的核心则是天子本人需要有深厚的根基与高尚的品德;二来,借卫武公刺历王之意,劝勉在位的君子为政以德。相较于《不苟》《非十二子》二篇引《抑》的侧重点均在个体修身律己方面,《君道》引《抑》则将目光放在了治国层面,虽然相较于前两篇在立意上有所超越,却也是《抑》的诗内应有之意,如诗的第二章:“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点明能够任贤用能,国家自然强盛,四方自然来归,这仰仗天子“有觉德行”,上可治国有序,下可为万民之表率。郑笺云:“竞,强也。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得贤人则天下教化于其俗。有大德行,则天下顺从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朱熹从天地人的角度出发,指出天子“有觉德行”为天下法,“言天地之性人为贵,故能尽人道,则四方皆以为训。有觉德行,则四国皆顺从之。故必大其谋,定其命,远图时告,敬其威仪,然后可以为天下法也”。可见这段诗文与荀子所欲表达之意相通,足见荀子引诗诗意漫布全文,非孤立、抒情地引用。因为荀子在此引《抑》所强调的德,既是“维德之基”的德,亦是“有觉德行”的德,二德本为同一“德”,前者更显君子有德傍身则“大形”备矣的逻辑关系,故荀子引之。 从《不苟》到《非十二子》再到《君道》,荀子三引“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我们看到随着所论述话题立意的拔高,“德”字的内在含义在不断变化,所言对象从君子上升到天子,正如《大学》所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荀子借《抑》言“德”正是言其“本”,本立而道生,“温温恭人,维德之基”之意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