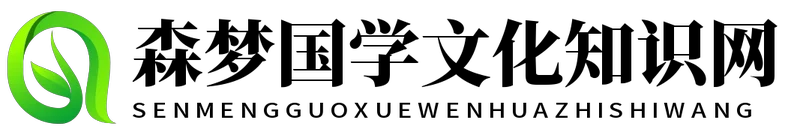摘要:近年来,以血缘为基础的儒家伦理遭受诸多指责和质疑。批评者认为儒家伦理只讲求爱亲而忽略了对陌生人的关怀。然而,这种判断乃是对儒家的误读,没有关注到儒家仁爱伦理的谱系及其演变问题。事实上,儒家仁爱伦理具有多重图式,它既仁爱建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同样也将之扩展到作为“陌生人”的“他者”,甚至是无生命的存在者。具言之,在传统儒家那里,仁爱伦理首先指向“血缘伦理”,其所强调的是爱从亲始及爱亲的重要性。然而儒家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时空的消解中又孕育了新的伦理形态。这主要体现在汉唐儒者所建构的“他者伦理”,凸显他者之于爱亲的“先在性”,延申了儒家血缘伦理的范围。而实现对儒家血缘伦理超越的是宋明儒者所构筑的“共生伦理”,此强调从一体之仁的视角去体爱万物,突破了传统儒家的血亲之仁。简言之,儒家的仁爱伦理非是囿于血亲之间,而是能普遍于万物之中。而我们通过钩深儒家“仁爱伦理”的发生图式及其谱系演变,或可以消除既往一些论者对儒家仁-爱思想所存在的误解。 关键词:儒家;仁爱伦理;发生图式;谱系;“陌生人” 引 言 如我们所知,儒家仁爱伦理建基于血缘之上,它强调爱亲的首要性和必要性。如此一来,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儒家仁爱伦理似乎只能局限地适用于有血缘的亲人(族)中,而不能适用于作为陌生人的他者。与之相关联的是,儒家伦理只是一种“私德模式”,“只能依照自身在差序结构中的位置运用私德,只能应对熟人和友人,不会形成一视同仁的‘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伦理,也就无法应对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甚至有学者以此断定“儒家本来就不愿意其原则在应用中成为普遍的,因为儒家所提到的‘人’并非‘所有人’或‘任意某人’,而是在特定私人关系和特定情景中的特定人。”所以这就造成了儒家与现代社会在本质上的不兼容。然而,细细考察儒家仁爱伦理的内涵及其发生机制就可以发现此说乃是对儒家伦理的误解。关乎此,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之进行了辨正,对我们理解儒家伦理的内涵多有助益。然而,这一问题仍有诸多可讨论的空间。故此,本文意在从儒家仁爱伦理的图式及演变来析理儒家所形成的三种伦理模式,以此来证明儒家伦理并不是囿于血缘的私德伦理,而是在其创生之初及后来的发展中都已经蕴含了对他者,甚至是非人之“物”的仁爱之情。同时,就此而言,儒家的伦理原则本身就已经内含了应对现代社会意义上陌生人( strangers) 问题的机制。 一、何以为亲:儒家仁爱伦理的血缘底色 “血缘伦理”是儒家伦理的底色,是儒家在建构其伦理学甚至其整个思想的大厦。历史地看,传统的血缘伦理由来已久,早在儒家之前就已经产生,之后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系统化,使血缘伦理在中国的作用更加显著,“终使‘血缘关系’成为了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的逻辑起点。”而伴随着儒家血缘伦理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即仁爱的“差序格局”也是理解儒家伦理的关键所在。这也是诸多学者批判儒家伦理不足以应对现代陌生人社会的症结所在。 如前所述,儒家伦理建基于血缘之上。那么,其亲爱的程度便和血缘的厚薄与感情的近疏有关。而血缘的厚薄和感情的近疏又与代际的变化有关,即代际越近,血缘越浓,情感愈深,反之则反。但大多数情况下,血缘所能“顾及”的往往是三代之内,再往后延申,大家的情感就很疏远了。这也是民间常说的“亲不过三代”的原因。在这里涉及两个关键信息,即“亲”和“代”,此二者直接关联着儒家血缘伦理的发生机制。那么,何谓“亲”呢?徐慎对之解释道:“至也。从见亲声。”段注:“到其地曰至。情意恳到曰至。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据此可知,“亲”就其引申义而言是指对象间的相即性,而其所最先或最优指向的就是父母,对父母之爱是人之情感最为极致所到处,这乃是一种自然且至极的情感。这便说明,亲便是指对父母之亲。再来看“代”,许慎对之解释为:“更也。从人弋声。”所谓“更”即使我们常使用的“更替”义,表示事物之变化。置换在伦理学的视域下,即谓血缘之情在代际间的演变。那么,我们从亲与代的维度来审视何以为亲,即是由于我们与父母属于血缘的“第一代”,是一种“无间”的血亲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态,在儒家的具体体现或者其理论依托便是“仁”。仁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其不但是一种德性的存在,从根本处讲乃是对血缘之情的表达,其包含了儒家的血缘伦理关系。儒家亲亲之爱及由之衍生的宗族、他者关系都是由之展开。所以,对儒家血缘伦理谱系演变的考察就无法避开仁。 在儒家,对仁的释义有很多,但通常认为其最为核心的内涵乃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所谓爱人,意指爱非己的他者,这是从广泛的层面来说。但是,结合儒家思想的系统来看,爱人(他者)之义,其首指并非是就“全体人”而言,而是偏重指向“父母”(兄弟姐妹)。《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所以为人在于有仁,而仁之优先指向于爱亲,此亲首要是指血缘最近的亲人,这所体现的便是儒家的血缘之情。如朱子云:“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即是强调仁之于爱亲的首要性。又“立爱自亲始。”同样意谓爱人其始义乃是说要爱我们的父母,或者至少要从爱父母开始。因为在儒家看来,爱亲(父女之间)是其他所爱的基础,亦或者说儒家所言的爱人之仁发端于人的血缘亲情(父母、兄弟)。“不孝不弟,虽有他善,终是不仁。何者?为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贵也。”即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即使在其他方面做的再好,也不能以仁许之。所以如此,即在于孝悌为本,其余的事情都是末,不孝不悌则大本已失,其余不足为道。这样的判定,便是上文所言的代际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父母生我养我,与我具有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这也就是亲之一代(无间)的表现。正是这种天然的内生血缘关系,使我们与父母处在一种“原时间”之中。于是,我们与父母的感情也最具原发性。如果对父母都不爱、不敬,不但是有悖于德与礼的,而且从更宽泛的层面来说,也是违于天理的,势必造成家国不宁的局面。故此,儒家是非常强调爱亲之于仁的原初义,反复畅言“爱莫大于爱亲”。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仁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这一根本的爱,便是儒家血缘伦理最基础,也是最显要的发生机制,它体现了血亲在人伦中的首要性和重要性。正是如此,儒家爱人的差等秩序及代际之分及由之所呈现出的“血缘谱系”才得以建构。 循前指,我们所以亲与不亲和代际的“隔断”与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代际的划分是基于血缘的远近与厚薄。这里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种,一是以“己”为中心,己之外的人(包括父母)都可以作为某代的存在。从这个向度来说,父母便是与我们相隔一代,但是此代却是血缘最浓的一代。二是,如果从亲缘的向度来看,父母与我们之间的“此代”并不能算“代”,因为我们彼此的血缘是直下而出的,有着天然的连接。“子女与父母的血脉相通,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在重要意义上是一体的,……两者以相依为命的方式‘共在’着。”父母之存在便是我们之存在,反之亦然。可以说我们与父母是一种“共构意义”的关系,二者没有时间-空间的隔断。诚然,无论从哪一维度来体察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无疑都是最亲的。那由自然地出生而来的联系必然先于其他所有的联系,也比它们更为稳定。“因为它是根据一些与本体直接相关的东西;至于其他的联系则是后加的,而且可能撤销。”所以,基于此我们才必须首先爱父母,再由之推到其他人际关系上。概言之,儒家血缘伦理具体体现在“孝亲”“友悌”上,这是儒家最为看中的两个内容。尤其是前者,更是最为核心和主要的。如孔夫子所说:“,入则孝、出则悌”是也。有子也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言孝与悌之于仁的重要性,这所反映出的是儒家的源初性的情感。 正是由于我们与父母所具有的这种非经验的天然之亲,是一种“血族生存相通的团结”的关系,所以,儒家乃至后来的中国社会都是是非常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体安性。如当宰我质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的时候,孔子便以“安与不安”反问之。因为,在孔子看来,父母与我们是最血亲的关系,“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不仅是生存上的血缘的传承,也是存在上的血亲之爱。所以,父母之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之身(情)的丧失。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我们之所以与父母最亲,原因就在于我们与之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是一种无法主动选择的、天生而自然的关系,不需要什么理由去解释它,血缘自然地使得我们与父母连接在一起。而与父母的这种血亲关系及由之所形成的家庭伦理是儒家思想的重中之重,是儒家伦理的第一基石,其他的伦理或等关系无不是由之展开。当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之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家庭或宗族之内的亲缘关系,其同时蕴含了爱他人(非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此也是儒家伦理的应有之义。下文将会详细分析。 二、何以不亲:时间-空间中血缘的消解及其表现 从社会群像的维度来看,与我们的父母家人共同存在还有所谓的熟人,乃至陌生人,这是我们无法忽略的群体。然而,从社会发展的机制来看,现在相对于我们而言的熟人或陌生人没准在很久之前也是我们的亲人。只是由于时代相隔太久,血亲关系淡化,彼此之间不再“认识”,似乎真的应了“亲不过三代”这句俗语。其实,这就关涉到“何以不亲”,即儒家血缘伦理的衍生机制与“式微”的问题。关于此,《礼记》已有所论及:“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郑玄对之注曰:“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也就是说,以己为中心所形成的三亲、五祖、九族构成了儒家的血缘谱系的基本格局。其中,最为亲的就是我们上文所述的上于父母,下于子女的关系。而随着代际的延伸,血缘就会逐层减弱,相应的情感也会淡化,直至成为陌生人。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此点,我们将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哲学要素进行分析。作为生命体,我们被抛在时-空之中。时间、空间作为我们直观的形式,是我们一切认识和活动的先天和必然的条件,这是就时间、空间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先天维度来说。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理解二者的伦理意义。“人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人的全部生存实践,……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的,所以,时间、空间和人的精神就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初级结构单元。”因此,对自我的认识与周围事物关系的考察无不需要藉此而来,对于代际亲缘关系的考察亦是如此。并且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这一问题,更有助于我们从义理上的深层次上理解其意义。 从儒家血缘伦理的发展来看,亲与不亲的关键就在于血缘的厚薄,这体现了亲缘关系的“圈层式微”状态。这种状态的发生与演变都蕴含并体现在了时空当中。首先,就时间而言,儒家血缘伦理的演变和“衰弱”又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其一是指“血缘的代际时间”。循前言,血缘作为儒家伦理的基点,其规定了儒家伦理的差序格局。它体现了儒家在面对父母、兄弟、亲人、陌生人时所流露出的不同情感。这差异性情感发生背后的原因在于血缘于代际中呈现的薄厚,即是说如果两个人(家族等)相隔的“代”很近,如我们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间,尤其是与父母,那么二者从发生意义上来说必然是最为相亲的,这也是儒家所以主张“仁自亲始”的原因。相反,如果彼此之间的隔好几重关系,代际也变得很复杂和疏远,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堂亲、表亲,甚至更远的关系。如《颜氏家训》云:“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虽然血缘的扩展对祖代的绵延有助,但代际的扩大,就意味着血缘的淡化,那么相应的亲情势必也会变得很淡。如此,彼此的血亲关系自然也会呈现出一种衰减或“消逝”的状态。 其二是“生存与生活的时间”。这主要是从现实和经验的视角来说,甚至是无关于血缘亲情,其所呈现的是“变化”的时间形态。而时间之变化意味着“一种否定机制,它将使现存状态丧失。”那么,所被否定的现在便是被抛弃的,其场域中所发生的一切物事都是被消解的。而从伦理的视角看,即是说“现代”与“原初代”的人之间处于“互相否定”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是没有联系的,那么自然无法加深感情。换言之,即使两个个体或公共体拥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在时间层面二者之间的相处和交流太少,那么于情感上同样会呈现出“不亲”的情况。简单地说,代际间的时间久远和亲人之间联系时间间隔久远,这两种时间因素共同造成了不亲的结果。 其次是空间的层面。空间是我们生存的场域,我们与亲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在此中完成。这里的空间并不首要指向物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就伦理学而言。即是说,我们与他人形成某种关系需要置于一定的空间内,而相互的生存使得我们感受到空间的道德意义。如我们所以与父母亲的原因,就在于孕育及生育的“无间空间”。“怀孕的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不只是或首先不是物理空间的关系”,而是源于父母与我作为“共在生命体”的伦理空间。这样,我们与父母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地近”的状态。故是,与父母相亲、相爱自然就不足为怪了。这是正面的分析。那么负面的分析,即是不相亲的原因,这便是时空距离的隔断,使得联系过少,最后甚至使关系处于断绝状态,自然不会亲。这也是为什么孔夫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原因。或就是怕相距过远会淡化彼此的感情。 此外,代际间的相亲同样是由于空间距离的近,彼此联系很多。因为在古代“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生产生活及情感所需要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种亲戚关系,因而使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亲代的可靠性就此显现。那么相反,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导致即使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戚,由于各样的原因,其所生活居住的地方彼此相隔太远,联系同样也会减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则更少,那么情感同样也会变弱。 此外,空间距离关系同样会反映在“代际血缘”中,即由于亲代之间相隔过久,从而使得血缘的疏远,即有点类似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心圆”模式:“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也愈推愈薄。”从空间距离的维度分析,己作为圈层的中心,其所发生的第一圈的波纹即是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此时血缘-空间便是最近的。而随着波纹的晕开,其离圈心的空间之隔距的越来越远,那么所造成的血亲“回响”也就愈薄。即休谟所说的:“距离削弱了想象和情感。”与之而来的便是亲缘淡化,情感消弱,即彼此不亲。 而时空中血缘亲情的消解,亦会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生活的各方面中。如就丧礼而言,血缘的远近决定了人们服丧之情及丧服的不同。如古代所施行的“五服”制度。“五服,斩衰至缌麻之服。”所谓斩“取痛甚之意。”主要是指至亲,如父母之丧所穿服质。而最轻的是缌麻,“谓之缌者,治其缕细如丝也。”这主要是指为关系比较疏远的亲戚所服丧之衣。这就表明儒家在代际间血缘的变化,“五衰之制,亲疏之杀也。”“杀”即血缘的消解,关系的淡化。甚至在儒家看来,血缘之情一般在六代的时候就已经“彻底”消亡。《礼记·大传》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所以,在传统儒家那里其实就已经意识到血亲于代际之间的差异和消解。 三、从血缘伦理到他者伦理的转换 如上所述,在面对社会的发展,儒家的血缘伦理的作用逐渐呈现式微的状态。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对我们生活影响的加深,其效用和表现不如“传统社会”那么明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就消失了。因为儒家血缘伦理在时间与空间中淡化与消解的同时,其又蕴含了某种创生性。这种创生性,以伦理的视角观之,即仁爱思想的普适性,继而形成了儒家的普遍伦理。所谓普遍性伦理是指,儒家所构建的仁爱体系并不是仅仅是局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血亲之情及其宗族之爱,而是“能够面对除了亲人、友人和熟人之外的一切陌生人,能够广泛适用人与人、自我与他者的各种关系。”甚至是一切事物。这俨然已经突破血缘之亲的范围,而扩展至整个社会,甚至宇宙。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儒家的血缘伦理不是消失了,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再细忖思,这种所谓的变化其实并非是一种新的变化,而是古来有之,只不过我们未予察觉。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儒家所讲的仁,虽然始于爱亲,但爱亲并不是仁的全部,仁亦不止于爱亲。换句话说,儒家并不是仅固守着血亲之情,只在自己的血缘小圈子里打转,而是注意到“内亲”和“外缘”的关系。即,儒家之仁及其所彰显的“亲缘伦理”。“儒家认为这种原初情感不限于父女间的私情,而是可以超越私情去仁民、爱物。”甚至有学者直接将之视为儒家伦理的基础。“仁为五德之首,实已含有他人伦理的维度。可以说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不但不是没有,反倒是构成儒家伦理的基础。”这早在孔子的思想中就有所体现。孔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句话,虽然首先讲的是对父母(亲人)之孝、兄弟之悌,这些都是基于家庭伦理也可以说是血缘关系来说。不过,此句后半段则就将仁爱扩展到“众”上,此众即使除去父母兄弟之外的所有人,甚至是“物”。皇侃注曰:“君子尊贤容众,故广爱一切也。”由此一来,儒家之对仁爱的论述绝非是局限于至亲之血缘伦理上,而是关涉到“陌生人”。与之相似的还有《论语》中之对兄弟的论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即言天下,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全球,皆兄弟即言如同血而亲者,即皇侃所疏:“既远近可亲,故不须忧患于无兄弟也。”这其实在说,对于非血缘之亲的人我们同样应该亲之爱之。此论同样是把血缘亲情推衍到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上。由此可见,从孔夫子开始,儒家对“陌生人”的问题就已经有所意识。并且,在其思想中,以儒家血缘亲情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三代”之外的仁爱伦理谱系,之后的儒者们又对这一谱系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孔子之后,孟子对儒家仁爱与血缘之情的阐释更为详细和切要。一方面,孟子固守儒家的血缘之情,强调爱亲之于父母兄弟的首要性,此是不可更易之纲领。这也是他所以批评墨子无父的原因。“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孟子看来,如若一味地讲求兼爱,便是视其至亲无异于众人,如此便相当于无父无母。但另一方面,孟子又将儒家的仁爱伦理扩大化,延至到非亲的陌生人。孟子曰:“仁者无不爱也。”“无不”即要“都”爱,这就意味着要爱包括父母家人在内的所有人。如其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里的“人”是相对于“吾亲”来说。吾之老及幼都是基于血缘之情来说,即是爱亲之谓也。而其所言“人”便是指那些与我“无亲”的熟人,或是相距很近但没有交集的人,或者直接是时空中完全的陌生人。而孟子认为,我们同样要以爱待之。除此之外,孟子又对“爱”的各个维度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除了上文之言的爱亲、爱人外,孟子又将之指向“物”,认为对物同样要爱。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孟子,甚至是孔子的思想中,虽然有爱物的向度,但此爱非是爱亲之爱,只是“功利意义的爱惜、珍惜之意,尚缺乏表示人际亲和情感的仁爱之意”。但是,无论怎么说,孟子确实更为明显地论证儒家的仁爱的普适性。由孟子所承继的仁爱伦理,不但形成儒家伦理的新格局,而且更进一步地将儒家的仁爱伦理推广到“万物”上。可以说,在孟子,儒家就已经有意识地突破亲之于血缘的界限了。 如果说先秦儒者对仁爱的阐述还是厚植于对血缘伦理的扩展,其重点仍是落在亲缘上。那么,到了汉代儒者那里,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他者伦理”,重视“类”之爱。董仲舒曰:“仁者,所以爱人类也。”不同于先秦儒者以爱“人”释仁的做法,董仲舒则从爱“人类”的视角去解释仁,这就突出了“类”的重要性,把仁爱的范围推衍到普遍人类或“所有人”上。在这样的语境下,董仲舒直接为仁的法则做了限定,“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即将儒家的仁爱落实在爱人上,而不是我。其又指出“仁主人,义主我也。”他通过辨别仁义的指向再次说明仁爱为何义。亦即“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所谓爱即是就“他人”而言而非己。当然,这里的人所突出的是全体之人,而不局限于亲缘之人。这是董仲舒对儒家之爱的裁定。 不仅如此,董仲舒更是在继承孔孟仁之爱物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证仁爱之于我、人、物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地揭示儒家仁爱的“泛血缘性”。“昔者晋灵公……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他通过批评晋灵公为己的自爱做法,指出真正的仁(者)应该是爱人。甚至认为爱人仍然不够,必须将爱体贴到物上才可以真正地谓之仁(者)。此处董仲舒所言的爱物则更多的是强调“亲情”或情感上的爱,由之“取消了仁民、爱物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使之变成了同质状态下的差异性秩序存在。”这样便更加凸显了儒家仁爱的普遍性,并弱化了传统儒家强调血缘之仁的做法。 同董仲舒论仁类似,刘向在对儒家仁进行释义的时候,也是沿着他者伦理的路数展开。“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这里,刘向通过区分大仁和小仁来说明何为真正的“大仁”。以其意,所谓大仁者是指那些能够将仁爱推衍到天下的人。细言之,即能够突破家庭之爱,把爱扩展到陌生人身上。而小仁则是指只是爱自己的妻子、子女,即具有血缘之情的人。而当二者冲突的时候,就需要舍弃爱亲之仁而偏重他者之仁。刘氏此言,显然“颠覆”了传统儒家所属意的爱必言亲的做法,而主张或应该把对“陌生人”的爱放在更为重要位置。由是,儒家仁爱的三代(家族)之偏重,反而成为了后置之为。 为了更好地彰显儒家仁爱之超越亲缘秩序的特点,董仲舒等人直接提出“博爱”的思想,“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把儒家之爱的内涵进一步扩大。董仲舒将博爱作为仁的内容,其意即在修正传统儒家仁之于代际性所存在的不足问题,而力求从广博的视角来理解儒家仁爱的内涵。这使儒家爱的层级性减弱,他者性增强。董仲舒以博爱诠释仁的做法,影响了后来的诸多儒者。如三国时期的韦昭,其在注释《国语·周语》时就直接道出“博爱于人谓仁。”晋袁宏亦言“博爱之谓仁。”较董仲舒而言,他们更为明晰地将博爱与仁相关联。当然,以博爱释仁影响最大的要数韩愈,其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同样也是从博爱的视角诠释仁。 通过上文我们对先秦-汉唐儒家仁爱伦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并不是仅仅在血缘之间,而是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一种他者伦理,更加注重对亲缘之外的陌生人的亲爱之情。汉唐儒者对仁爱伦理的阐释,不但消融了儒家以血缘为基础的仁爱秩序,而且突破了儒家仁爱的代际范围,甚至还延展到其他物类。如此,当我们再回顾儒家仁爱范围问题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儒家仁爱思想只适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而不能应用于陌生人。实际上,儒家仁爱伦理发展至汉唐,其不但坚守儒家的基本观点,更在其基础上将亲爱之仁延申到亲缘之外的他者。由之,儒家的血缘伦理开始倾向于他者伦理。这是儒家伦理发展的又一形态。 四、一体之仁与共生伦理 汉唐儒者对儒家仁爱的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儒家以血缘为根蒂的仁爱伦理,把血缘亲情推衍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他者身上,并更加偏重于后者,转变了儒家伦理的演说方式和实践法则。而实现儒家仁爱伦理“哥白尼式”转换的要归于宋明儒者。他们在继承汉唐儒学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儒家仁爱伦理的发展,将之衍变为“共生伦理”。共生伦理的基础是“万物一体”,其理论表现便是“一体之仁”。这可以视为理学家们的某种共识。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此北宋以来理学家精神命脉之所寄也。”陈荣捷先生亦言道:“万物一体之理论,为宋明理学之中心。由二程子经过朱子、陆象山以至于王阳明,莫不言之。”即是此意。 如上所示,宋明儒者言仁是以万物一体为始基,其意便是要突破先秦儒者以血缘来处理人际关系做法的局限性,而转向从“一体”的视角来重新诠释仁爱伦理,以此擘画出儒家伦理的新图式。如张载所言:“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船山对之释义为:“则天下之物与我同源,而待我以应而成。”即是说物我无二,同源而生,其归为一。张载更进一步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率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此是从血缘的角度而论,意即我与物具有血亲关系,是一种家庭成员关系,万物便是我的同胞兄弟,甚至可以说即是我自身,这就从根本上消融了先秦儒者以血缘别人我的做法。换句话说,在张载,其所论证的仁爱不是生存上的爱惜之情,而是存在论的价值情感,即将万物视为与我具有同血缘关系的存在者。可以说,张载以“民胞物与”的即情模式开启了理学论证共生伦理的先河。 与之相似,程朱亦沿着这一理路展开对“同血共亲式”仁爱思想的阐释。程颢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其接续前儒之论,仍把仁作为核心思想。不过,不同于前儒以从爱人的维度解释仁之内涵,其是从万物一体的层面加以阐发。这同样消弥了前儒以血缘论仁爱所存在的局限,而使儒家血亲思想得以拓展。其又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在物我同体为亲的基础上,程颢又将万物视为吾之一体,以期泯除己与物的对立,将存在的体外之物纳入我的生命之中。其意识到吾之个体生命意义的完满须是与物同在的,此即“由浑然一体而无隔以示仁体之无外,此正表示真心仁体之觉健与无窒滞。”这所彰显的是儒家伦理的共生性。之后,程朱理学的学者多是在继承了二程所构筑的“一体之仁”思想,重视从万物一体的角度理解仁。如吕大临认为:“仁者以天下为一体,……人之所以不仁,己自己,物自物,不以为同体。”除了对仁之于万物一体的论述外,吕氏也解释了为何不仁的原因,即将物我二分,不能认作一体。质言之,即只将仁爱局限在“我(亲)”的小圈子内,不能普遍爱之。 朱熹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运思,其认为:“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尽也。……仁之为义,偏言之则曰爱之理……专言之则曰心之德。”朱熹较为自觉地注意到儒家仁之内涵的广泛性,认为不能一言说尽。如果概而言之,即是爱之理与心之德,二者又分别是从偏言和专言的角度来说。其中,朱熹又很重视以天地之心论仁,“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者也。”从生-心的角度诠释仁,此生便是包含所有物之生,亦是共生之形态。于此基础上,朱子接续二程等人的话头说道:“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即认为天地和我是为一体,我之生存与行为便是天地(万物)之生存与行为。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就要革除物我之分,“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此论与吕氏相似。 阳明对此问题的论证更是直接和明晰,他同样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即以天地的视角来思考物我关系。其对仁的诠释也是基于万物一体的角度,“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恻怛”源于孟子之言“恻隐”,即是以仁爱人。于阳明,其是从“全体”来说,非是限于亲人或熟人,即不在代际与血缘之内,甚至不惟人类,而是包括物在内的一切。如果对此细而论之,在阳明,其先是突破儒家血缘伦理的代际关系,主张亲无内外,“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即要像爱亲一样爱其他人。接着,其又从超越类的角度论证儒家的仁爱: 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一体之仁也。 阳明循着同类→知觉→生意的层级详细地阐述了仁爱的“一体性”,这一层级与“我”之(血缘)关系逐渐淡化。而正是在愈来愈淡的关系中能够行仁,这恰恰反映出儒家仁爱伦理的“共生性”与“普遍性”,也是阳明所以如此论证的目的所在。以其意,传统儒家认为爱亲之谓仁,即是从血缘的亲疏加以表现。而他以孟子之言孺子之入井的故事为例,说明在面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婴儿在将要掉入井中时,人所起的怵惕恻隐之心便是仁。这就意味着儒家的仁爱并不是囿于血亲关系中,而是同样适应于陌生人。循孟子论证的理路可知,我们之所以能够爱非亲非故的陌生人,这或许还可以从我们与之同类的角度来解释。再往外推一步,当我们面对鸟兽之哀鸣觳觫时,还能有不忍之心,即说明我们的仁爱能够触及非类的动物。这就已经打破儒家仁爱的类属性。然而,阳明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又从草木之折、瓦石之毁的视角来说明仁,认为我们在面对无生命之物的时候,同样能升起仁爱之心,此即表示仁爱可以遍及万物。阳明最终要说明的是儒家仁爱不但具有超越具体的血缘、代际及人类,甚至可以超越有生命的物体的特性,能够遍及和适用于所有存在者,可以说这是一种“天下主义伦理学”。 宋明儒者通过辩证地搥提儒家的仁爱内涵,不断地将之适用范围扩大,此种推衍不是无情感的机械式拓展,而是将儒家血亲伦理灌注其中,即在爱人、爱物的时候,是以一种爱亲的态度为之,二者不是异类的相通而是情感的共生。质言之,“他们将这种血缘亲情泛化为一种充塞天地的普遍道德情感。”这不但突破了儒家血缘伦理的圈层局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出了一种新的儒家伦理模式,即“共生伦理”。之后的儒者们便延续这一提法,都注重从一体与共生的维度去诠释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说,宋明儒者重塑了儒家的伦理形态。 那么,当我们从儒家仁爱-关系伦理自身所蕴含的发展规律,再审视既往论者所怀疑的儒家仁爱伦理只能适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无法顾及其他存在者(陌生人)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此论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们仅关注到传统儒家伦理的一种图示,而没有看到其在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其他伦理形态。正如上文所论的宋明儒者所构建的“共生伦理”,就已经自觉地对亲代之外的他者予以仁爱关怀。 五、结语 当然,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传统儒家仁爱伦理的立论基础来看,学者们对儒家仁爱伦理进行讨伐或批判有其可被理解性。因为,一方面,儒家的仁爱思想确实厚植于血缘之上,强调血缘的重要性,爱亲的先在性;另一方面,随着代际的延展,即使那些原本具有血缘之亲的人,彼此的亲爱感也会被削弱,更不用说去仁爱那些本来就是非亲的存在者。这样就会给人一种儒家伦理只能局限地处理亲人(熟人)关系,而无法面对陌生人的感觉。故此,由之所衍生的对儒家伦理原则外生性效能不足的批判,从古至今从未停止。然而,从义理上来说,这种批判并不能成立。或者说,此言并不符合儒家伦理的发生模式,也未能充分而全面地理解儒家的仁爱伦理思想。因为,这毕竟只是儒家伦理叙事的一个维度,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其他的呈现图式。基于传统儒家仁爱原理的预设,其在强调“爱亲”的时候,本然地就将爱他者纳入所考虑的范围。当然,这其中必然是有仁爱秩序的差异。因为奠基于血缘的情感之爱其天然的具有优先性,同时泛血缘共情的互通又蕴含了“推移”的可能,然而这种推移每更进一步便会使之关系大为减弱。另外,于事实层面,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已经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对自身的理论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就伦理谱系而言,由先秦的血缘伦理演变为直接地应对血缘之外的陌生人的他者伦理,甚至将他者亦或是陌生人视为更为重要的伦理指向。宋明儒者更进一步,他们不但实现了对儒家血缘伦理的突破,而且亦打破仁爱之于人类的局限,将之扩展到万物的层面,从而实现了儒家仁爱伦理的“共生性”,可以说这是儒家伦理史上的里程碑。而从“一气化生”的视角看,甚至可以说“陌生人”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万物从其大本大源上说并无差别,那么就无所谓亲人、熟人、陌生人了。 综合儒家仁爱伦理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不但是具象的,同样也是普遍的。就普遍性伦理而言,它“是相与之道,是交往之道,它建立在天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与人等一般的关系世界中。”是适用于亲人及其之外的所有人物的伦理。质言之,儒家所建立的伦理学说,是能够面对除了亲人、友人和熟人之外的一切陌生人,能够广泛适用于人与人、人与物等各种关系之中。 作者:王闻文(1997—),男,河南周口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伦理学研究。沈顺福(1967—),男,安徽安庆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