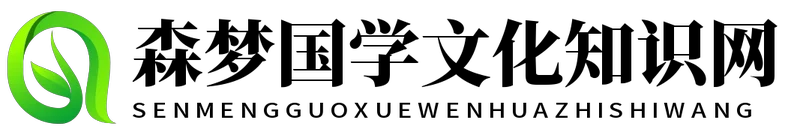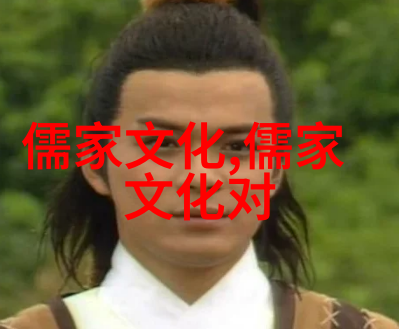摘要:《孟子正义》是清代学者焦循探讨人性论和思想的代表作。在书中,焦循根据人可以教之仁义的事实,论证人性本善。人性由本于血气形能的欲、情、知共同构成,三者发用中出现的弊端只能依靠知的向学工夫来补救。仁的彰显扩充依靠知的活动,运用知追求“合宜”的生活乃是人道的基础。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人道经历了不断的通变,圣贤所标举的执中时行、注重日用常行和为民造命等原则代表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方向,对后世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焦循是清代扬州之学“由专精汇为通学”①的代表之一。他的学问承接吴、皖二派,博大精深,无所不通,尤精于《易》与《孟子》。焦循于易学提倡“实测”,注重发掘《易》中的“旁通”“时行”“相错”诸例;于《孟子》则推重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以赵岐注为基底,以戴氏的义理探讨为准心,广泛征引有清一代六十余位学者的著述,将《孟子》的人性论、思想与焦循本人独具特色的《易》学融贯一体,形成了饱含济世情怀而又颇具思辨特色的儒家思想。 一、人性善的论证 戴震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于《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三书,而以《孟子字义疏证》完成时间最晚、思想最为成熟②。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引述构成了焦循疏解《孟子》的思想主脉和理论依托。概而言之,戴震言理不出于人情人欲,言性不离于形质才能,言人道则贯通仁智而重仁政之施,其思想可归结为“推己反躬、忠恕絜矩、通情遂欲”③。《孟子正义》在此基础上“依句敷衍而发明之”“绘本义于错综之内”④,对《孟子》的义理进行了全面而富于时代特征的解读。其中,人性论奠定了伦理和思想的基础,是焦循疏解《孟子》的一大重点。 在“生之谓性”章,焦循引述《孟子字义疏证》云: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成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孟子正义》,第739页) 焦循又引程瑶田的《通艺录》作旁证:“有质有形有气,斯有是性,是性从其质其形其气而有者也。”(同上,第741页)戴震以天道无外乎气之运行,由阴阳五行气化而成的血气心知为人的一切德性与知能的基础。程瑶田则强调气化形质之前并无悬空无着的“性”,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本根的意义上,气化形质是性的来源、依据。在论“性无善无不善”章,焦循引入戴震关于“性善”的讨论,指出泛泛而言的性为“飞潜种植之通名”。 “知其性者,如其气类之殊,乃能使之硕大蕃滋”(同上,第751页)则表明,“性”是对一类植物/动物由禀气之殊而形成的能力之内涵与边界,及因此与外在环境形成的种种固定关系的理解。由此获知的事物之“性”无甚抽象内容,然如能对这一本于气化的自然有“明于其必然”的理解,则关于“性”的讨论可超脱杂乱浮浅的现象知识的无序积累而成为对一类植物/动物“协乎天地之中”⑤的存在之状的概述。 更进一步,物性只有与他物、周围环境的“宜”与“不宜”,无所谓善与不善。善与不善专属于对人性的理解。因“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⑥,故孟子有“性善”一语,而人禽之辨的关键落于“知觉”。知觉之异,本于形色。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焦循对“明于庶物”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并进一步探讨人禽之别: 庶物即禽兽也。“明于庶物”,知禽兽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义也。同此饮食男女,人有知则有伦理次序,察于人伦,知人可教之使知仁义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故去之。舜能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故存之。性本知有仁义,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义行也。若禽兽性本不知有仁义,而强之行仁行义,则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义者,君子教之使知,则庶民亦能知仁义。庶民知仁义而行之,亦是由仁义行,非强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义也。此庶民所以异于庶物也。(《孟子正义》,第568页) 这段话指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可不可教之使知仁义。伦理次序普遍地为一代代“庶民”所知晓、尊崇,却从未在动物群落中产生并得到认可,焦循依据这一历史事实,推出人与禽兽在本性上有着根本不同,故对庶民的教化,不同于对禽兽的“强之”。仁义之初起,本于伏羲、尧、舜等圣人的“存之”。这种“存之”是一种深刻的自觉,使得蒙昧的人类社会迎来了一线光明。在“滕文公为世子”章,焦循再次阐述了圣人作为先觉者的意义: 圣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已之性既能觉于善,则人之性亦能觉于善,第无有开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则不能觉;己能觉,则己之性善。己与人同此性,则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觉,必待先觉者觉之。故非性善无以施其教,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孟子正义》,第317页) 人同此性,即同有善性,而人性之善依然有待于“通”。“通”意味着被障蔽者得以开显,被阻塞者得以畅达。圣人的自觉是一种自我开通,而庶民的“通”则始于教化。一代代圣人君子不断的自觉与存性,累积凝结为“人道”,使得暂时不能自觉的庶民经由教化而获得了觉其性、存其性的通途。需要注意的是,君子所存者,并不直接是仁义,而是性中能觉己性的“自觉”本身,能“通”性善的一点灵明。这是一种基源性的知能,它构成一切向内、向外觉知的基础。在“生之谓性”章,焦循引用《孟子字义疏证》,指出人、物受天地气化而成性,性呈现为千差万别的形能运动,其中有血气者的性,可概称为“知觉”: 凡有血气者,皆形能动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质各殊,则其形质之动而为百体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心之所通曰知,百体皆能觉,而心之知觉为大。凡相忘于习则不觉,见异焉乃觉。鱼相忘于水,其非生于水者不能相忘于水也,则觉不觉亦有殊致矣。……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不全也。仁义礼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极其量也。知觉运动者,人物之生;知觉运动之所以异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无有不善”,以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孟子正义》,第740页) 焦循在“尽其心”章亦指出:“尽其心即极其心。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谓知其性之善也。”(同上,第877页)气血形能是性的基础,性无有出于“知觉”之外的内容。“知觉”包含甚广,而以“心之所通”最为深广丰富,因心知最具觉的能动与灵明,故可以“极其量”,历史化地展开为仁义礼智的条理;仁义礼智的充分展开与高度调谐则被视为“神明”。 戴震指出:“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时,及其无蔽隔,无弗通,乃以神明称之。”(同上,第769页)又,“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高明配天”(《礼记·中庸》),神明是对人性本有之善扩充至于理想境界的概括。鸡鸣为辰、虫鸟为候之类的性是本于形体、亦限于形体的;心知与之不同,可向极为深广的领域扩展,以至于人仅知其量能扩能极,而不能预其极量何在。 故“仁义礼智无不全”的神明之境乃为一理想,而非现实。可以说,戴震从现实中所呈现的现象来探讨性,而不限于现实;他强调心知的“通”“明”,指出心知不限于现实中的已在,更有潜在的知能。未在而潜有的知能更加敏锐地向我们指示出心知的本来之状。 焦循延伸了戴震关于人禽之别的讨论,在“性犹杞柳”章,《正义》云: 盖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岂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贼之以为桮棬;人之性,但顺之即为仁义。故不曰戕贼性以为仁义,而曰戕贼人以为仁义也。比人性于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将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祸仁义,而孟子所以辨也。 杞柳之性,可戕贼之以为桮棬,不可顺之为仁义,何也?无所知也。人有所知,异于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变通,异乎禽兽,故顺其能变者而变通之,即能仁义也。杞柳为桮棬,在形体不在性,性不可变也。人为仁义,在性不在形体,性能变也。以人力转戾杞柳为桮棬,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顺人性为仁义,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转戾也。(《孟子正义》,第734-735页) 这段话统合了人禽之别、圣人先觉与教化可行的讨论。焦循认为,仁义皆本于“通”。“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是超越个体形骸隔限而获得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解的基础;而这种人心之间基本意向与情感的相互通达,以及本于人己关联的对“人性”的理解,构成了人与人相互亲近、相互承认的“在关系中存在”的基本方向,亦即“仁”的原始内涵。 “义”的含义则更多指向“时行”⑦或因时变易:“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在人与事物广泛沟通并受其影响和塑造的过程中,人能够发挥心的“变通”之用,知解种种与事物的关系对于自己“宜”或“不宜”,进而主动向着有宜于己的方向转变,此种变化亦是“利”。可见,焦循对“义”的理解也颇有新意。 经由上述讨论,“通”的含义不再局限于圣人的向内自觉,而扩充为涵盖了人与己、人与物之关系及其理解的“变通”。“变”之一字,饱含历史的意味。而“变通”的本性,决定了人不能不通于他人、通于外物、通于变化中的世界。教化是顺此可变通、能仁义的人性而为的,绝非如制器那样屈抑、裁割物形,戕贼物性。 通、觉、明等观念同样为佛、道二家所运用,如何能够凸显其中的儒家特征?仁义之发见,本于人性的变通、自觉,故在逻辑上不可用仁义来包纳通、觉、明。因此,在“居下位而不惑于上”章,焦循突出了“思”: 不诚者,非天不以诚授我也,是我未尝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诚身而归重于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诚既明矣,又思其诚。……惟天实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实有此善,而物乃可动。诚则明,明生于天道之诚;明则诚,诚又生于人道之思诚。人能思诚,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诚也。(《孟子正义》,第510-511页) 孟子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思”在儒家性善论的传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焦循运用“思”将前述材料中的通、觉、明等观念进行整合;因“思”本身含有能动的、主宰的倾向,故能将通、觉、明这些观念显见地包纳进儒家思想的范围之内。在《孟子》中,诚明关系的讨论落于思诚,焦循借此指出,思则能明善,且思由诚而来。 然而,无思之诚只是一种本于天命的善性的假设,无诚之思则必定不是思的本来样态;思因其渊源于诚而必然以思诚、明善为其活动的第一原则。思既是诚得以开通为现实的、活动的人性之善的枢纽,亦是施行教化而能不离其本的首要依凭。所谓“非性善无以施其教,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其中心即“思”。 二、欲、情、知的统合 焦循在探讨人禽之别的过程中触及了性善论的中心问题,也就不得不处理《孟子》文本解释传统中的相关核心概念。《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章、“牛山之木”章在讨论人性的过程中,涉及性、情、才等概念。这些材料经由宋儒的解读,成为理学中阐发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重要依据,性、情、才的定义及其关系也成为理学人性论的支柱。戴震、焦循为扭转理学对人性的定义,阐发自己的人性论,就需要重新梳理上述概念。在“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章,焦循首先引用《孟子字义疏证》,区分了欲、情、知: 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声色臭味之爱畏以分,五行生克为之也。喜怒哀乐之惨舒以分,时遇顺逆为之也。美丑是非之好恶以分,志虑从违为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孟子正义》,第754页) 戴震指出,情、欲、知皆本于血气形能的自然。其中,情接物而发,一方面关乎声色臭味的满足,一方面关乎美丑是非的判别;而欲中的爱畏,知中的好恶,仍属情的范畴。可以说,情贯通于滋养生命的欲和达致圣贤境界的知之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之一。欲的展开方向,来源于五行运化在此类生命中形成的构造,“有所限而不可踰”(同上,第993页);情的发动,受个体在时遇中的处境的驱动;知的提升,则完全在人的知虑营为,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根据焦循对“仁义”的阐述,人不仅能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还会在时遇的变化中“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因之,被动的欲的满足、引导和节制,以及受时遇驱动的情的疏通、拨转和约束,必然依靠知来完成。而知的活动,其目的终究不外于欲和情的畅遂。在此基础上,焦循结合《论语》,继续探讨情、性、才的关系: 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贞言性,情利者,变而通之也。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己之好货,而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因己之好色,而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如是则情通,情通则情之阴已受治于性之阳,是性之神明有以运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为善,而决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运旋其情欲,使之可以为善者,才也。(《孟子正义》,第755-756页) 旁通首先以己身之欲作为基础,去觉知、理解、肯认作为同类的他人之欲。人群中同类之欲的相互通达、肯认乃至和合实现,又必然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沟通、共鸣与调谐。此调谐过程条理化为人所共由的遂欲达情之途——人道,而人道作为普遍化的条理,依然是繁多的、现实的、活动的欲和情的条理。旁通包含了欲和情,焦循在“情之阴已受治于性之阳”中用“情之阴”这一传统表述概括了欲和情。而“性之神明有以运旋乎情欲”则进一步指出,并非别有一种超脱情欲的“神明”对情欲加以钳制,而是心的知觉扩充为仁义礼智的条理并使情、欲的发动受到范导。 因此,虽有“神明”“情欲”的命名之别,欲、情、知三者在根本上源于一物,统归一体。情、欲受到范导而“可以为善”,就证明了它的非恶,同时也能反推出人性中本有思诚向善的知觉。这就是焦循解释下的孟子性善论。根据戴震所说,“孟子所谓性,所谓才,皆言乎气禀而已矣。其禀受之全,则性也。其体质之全,则才也。”⑧“才”是对禀气所得的形体及其作用的全面概称。这样,《孟子》文本中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得到了解答。顺之而来的问题是:“人何以有不善?”焦循认为: 不通情而为不善者,无才也。云非才之罪,犹云无才之罪也。盖人同具此神明,有能运旋乎情,使之可以为善。有不能运旋乎情,使之可以为善。此视乎才与不才,才不才则智愚之别也。智则才,愚则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运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达,圣人乃立教以达之。(《孟子正义》,第756页) 焦循将“非才之罪”解为“无才之罪”,将可以为善而终不能为善的问题,转化为智愚问题。“形色即是天性”(同上,第938页),不能为善者虽有人形,却不能自行开发其本能变通的知觉本性,以至于行为不合仁义。此为禀气差异所致,圣人教化正为此立。焦循引胡煦《篝灯约旨》云:“盖贤不肖皆有为立事之后所分别之品行,而智愚则据性之所发而言也”(同上,第735页),正是此意。《孟子字义疏证》亦云: 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钜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则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又有明暗,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失理者,限于质之昧,所谓愚也。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孟子正义》,第769页) 戴震将人心知觉能力的高下不同,比喻为火光照物的明暗之别。照物失察、多有疑谬谓之失理,失理源于禀气而得的知觉不足,这种先天的禀赋之别可以通过后天的为学来弥补增益。因此,人性善不善的问题,取决于人的能不能知。如戴震、焦循所言,人可以知仁义、立教化,人类群体在历史中的活动显示出其具有不同于禽兽的知觉,这表明人性在普遍意义上因具有能知仁义的知觉而是善的;但这种普遍的善,只是对现实中不同气禀的个体知能状况的一种归约,人性的探讨总是从对现实而具体的个体的知能的反思入手,并在对个体的现实与类的潜在之能的理解或设想中承受着张力而展开的。生质蒙昧以致愚迷仅是个体不能为善的原因之一。根据欲、情、性的结构,人不能为善的原因是: 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喈礼义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知也。(《孟子正义》,第754页) 这里对欲、情、知三者的论说看似平列,实则有重点。欲之失源于人只知己欲,而对他人的基本欲求不能旁通,甚至视之如仇;情之失源于人偏于一情,使喜怒哀乐的自然发动受到阻滞而无法顺利流转,以致违离人情的常态。对欲、情的补偏救弊,只能依靠知的主动疏通引导。而知之失正是上文所说的障蔽愚迷,其开解依然依靠知的向学工夫。因此,人不能为善的原因有三种来路,而其解决之道则全归于知,全结于学,即“知觉既有智愚之殊,而熏习复有邪正之异,于是智者习于善则愈远于愚,即愚者习于善亦可远于本然之愚。”⑨这是戴、焦对孟子性善论中的修养工夫的发展。 在“告子曰生之谓性”章,焦循引入《礼记·乐记》对人性的讨论,进一步解释“知”对于人性的重要意义。其云: 《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人欲即人情,与世相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以所欲所不欲为仁恕之本。“人生而静”,首出人字,明其异乎禽兽。静者,未感于物也。性已赋之,是天赋之也。感于物而有好恶,此欲也,即出于性。欲即好恶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为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兽知声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恶丑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恶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恶腐也;非不知声,不知好清而恶浊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异于禽兽之欲,即人之性异于禽兽之性。(《孟子正义》,第738-739页) “欲”的生命活动,推动着人的知、情向着各个方向发动、衍生,而这些方向可以高度概括为“好”“恶”。“好恶”蕴含着忠恕的基础,此为人有别于禽兽的最初端倪。端倪的扩充依靠知,焦循特别将“物至知知”解释为人的能知可以不断扩充,一知而再知,非如动物的知那样有限。人的欲、情能够“与世相通”,个体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不断将其本性展开为内涵愈加丰富的忠恕之道,关键就在于心之知觉本有的知的能力。当然,知的运用也会出现穿凿之弊,这是历代圣贤不断对既有的礼乐之道加以变通的原因所在。因此,孙邦金等学者指出,焦循的“知”并非简单的客观认知,“而是一种综合知(判断)、情(感通)、意(取舍)为一体的,‘转识成智’之后的人生智慧”。⑩ 在以上讨论中,知成为性善论所以成立的关键,而遂欲达情仍是知的最终目的。戴震甚至说,人欲如能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又说“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11),把欲的满足、情的畅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口之于味”章,焦循引《孟子字义疏证》指出: 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则命之谓也。仁义礼智之懿不能尽人如一者,限于生初,所谓命也,而皆可以扩而充之,则人之性也。谓者,犹云藉口于性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谓性,即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体之于安佚之为性;所谓人无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为善,即血气心知能底于无失之为善;所谓仁义礼智,即以名其血气心知,所谓原于天地之化者之能协于天地之德也。(《孟子正义》,第992页) “谓者,犹云藉口于性耳”是戴震借用《孟子》原文阐发个人思想的关键。仁义礼智“谓”性是为了指引人将心之知觉视为人独得于天的本性,而全力扩充之,不因生初气禀的差异而自限不进;声色臭味“谓”命是为了指引人接受形体之欲所受的命分之限,在追求满足的过程中知止不殆。“谓”暗含了孟子对人性的欲、情、知的判别;仁义礼智谓性的论断,是为了引导大多数人获得对于人性的一种“应然的”理解。此举颇能显示儒家以名正实的思想方法。 后儒将仁义礼智与声色臭味截然二分,以为二者确有不同的来源,戴震认为这是对孟子意旨的严重误解。欲、情与知皆源于血气、禀于生初,均是性,亦均是命。这才是三者的实然。他进一步说,口目耳鼻四体的欲即性,人能运用知来引导、限制欲,使之得到合理满足而不踰界限,就是性善。这也就是焦循所说的“以性之神明运旋情欲”。在戴、焦的论述中,仁义礼智不仅不能脱离四体之欲,甚至还以四体之欲的畅达满足为其主要内容。焦循将这一思路从个体推至群体,从抽象的心性论推向具体的历史变迁进程,由此展开了以“旁通”为特色的思想的讨论。 三、“利”字新解 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善,与基于此种人性的理解而被创设、传承、损益的人伦之道,因忽略却又无法脱离欲和情而成为侈谈性理的空中楼阁。在“告子曰食色性也”章,焦循指出: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饮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禽兽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饮食男女,圣人教之,则知有耕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异于禽兽者,全在于义。义外非内,是人性中本无义矣。性本无义,将人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义同比桮棬,则仁亦在性外,此分仁义言之。(《孟子正义》,第743页) 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焦循引《孟子字义疏证》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同上,第234页)饮食男女是天道流行所昭示的生生之德在人身上的具体呈现,是人类群体的延续和团结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人道是在对具体的饮食男女之欲进行调整、引导而求其宜的过程中产生的,禁绝人欲,实则走向了人道的自拔其本、自我取消。戴震因此反对宋儒“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而必禁绝之的“理欲之辨”,视之为“忍而残杀之具”(同上,第503-504页)。 戴、焦一致认为,“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同上,第772页),使民众得以达情遂欲是统治者施世的主要目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应该放在“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的前提下来讨论。这种基于欲情的推己及人,在思想上督促居于高位、占据优势的统治者将保民若保赤子看作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为儒家传统的伦理提供了一种颇具清代思想特色的人性论依托。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的注文指出,人性之善,或者说人能扩充其心知而使欲的满足合乎人群协调发展的要求,“全在于义”。告子的“义外说”将人物比而同之,降低了仁义的地位。仁与义,或仁义礼智四者是不可剥离开来的。在对“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进行注解时,焦循引《孟子字义疏证》云: 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赅义,使亲爱长养,不协于正大之情,则义有未尽,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赅礼,使无亲疏上下之辨,则礼失而仁亦未为得。……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其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凡仁义对文,及智仁对文,皆兼生生条理而言之者也。(《孟子正义》,第234-235页) 焦循运用“旁通”“时行”“当位”“失道”等易学概念来解说仁义礼智,见于《易通释》等著作,(12)其论述以《易》中的象辞关系、卦爻运动为基础;而对仁义礼智内涵及其连通关系的直白阐释,则借助于《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对仁义礼智关系的讨论,合乎宋代以来“仁包四德”的传统,而尤其强调仁义礼智作为“德”是对气化推行见于人心的条理的指明,“气质之性”以外无所谓性,无所谓德。 在仁义礼智四者中,仁占据基础的、根本的地位,是天道生生不息的运动在人之一身的凝结和呈露;而智是人心对其本具的生生之德的自觉,及对仁的内涵的有条理展开。智无仁则无所根据,仁无智则晦暗不彰;仁如不能经历智的自觉而被有意识地视为人道的内在基础,则无法作为生生之德在人的存在中展开,人类将与禽兽无异。可以说,心之知觉条理化为仁与智的德性,仁与智互为基础而在其展开活动中相互揭示,是戴、焦人性论的重点。 在仁智关系的探讨中再次凸显智的重要性之后,焦循将另一个讨论重点置于“义”的阐述上。《易·乾·文言》有“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等语句,为义与利的通贯提供了文献依据。在重情欲的人性论和儒家经典的共同支撑下,如何理解“利”成为焦循伦理、思想中的一大要点。《孟子》合言“性”“利”的部分在“天下之言性”章,其云: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此章一直是《孟子》解释史中的一个难点。焦循对此章隐微之义的发明,则关联于其《易》说而独具精彩之处: 正义曰: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旨,与前“异于禽兽”相发明也。《易·杂卦传》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谓已往之事。当时言性者,多据往事为说,如云“文武兴好善,幽厉兴好暴”,“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及《荀子·性恶篇》所云“曾、骞、孝已,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秦人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皆所谓故也。孟子独于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贞”之利。《系辞传》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利以能变化,言于故事之中,审其能变化,则知其性之善。利者义之和,《礼记·表记》云:“道者,义也。”注云:“谓断以事宜。”《春秋繁露·仁义法》云:“义者,谓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变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与禽兽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无论贤智愚不肖,皆变化而知有夫妇父子;始食鸟兽蠃蛖之肉,饥则食,饱弃余,神农教之稼穑,无论贤智愚不肖,皆变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为利也。于故之中知其利,则人性之善可知矣。 《系辞传》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云:“又明于忧患与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传云:“通变之谓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变不足以言事。诸言性者,据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恶,言性善恶混,或又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皆不识故以利为本者也。 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农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为善,于此括全《易》之义,而以六字尽之云:“故者以利为本。”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此利不利之间,利不利即义不义,义不义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则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则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兽也。几希之间,一利而已矣,即一义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孟子正义》,第585-586页) 焦循分解了这段话的层次。首先,“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是对以往各种人性论成说来源的概括。“故”指历史中种种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浅表的、局部的归纳,则产生了性无善无恶说、性善恶相混说及荀子的性恶之说。这些理论不仅未能恰当地理解现象,还徒增误解。唯有孟子独具慧眼地指出,“故者以利为本”,在审视历史中的人类活动并试图由此获得关于人性的理解时,应从“利”的角度出发,照察和反思历史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通变”之事。 接下来,焦循顺势引入《周易·彖传》《系辞传》的内容,展开关于“利”的讨论。根据“元亨利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等论述,“利”是人的特有知觉——心知活动扩充产生的一个面向,它在人类历史里不断发生的以“通变”而求“合宜”的过程中一再呈现。《礼记》和《春秋繁露》的引文共同表明,义是对事之在我是否合宜的一种裁断,是“我”对事我之关系的判断,而非孤悬于人心之外的准则;而事的宜与不宜,仍归结于“利”。“利”是对义的内涵的明白而无偏向的呈露,它不仅包含饮食男女的基本欲求,更包含火化粒食的知的进取与夫妇父子的人伦秩序的规范化,是人的各类活动不断变化而未曾脱离的一个基本轴心,标识着人对自身生活朝向更好、更为协调的方向的期待。 因此,“利者义之和”,虽然义常常被认为是求利活动的规范和导向,但在更基础的,与人类能知觉、能感通的本性更深切相关之处,利为义奠基。义作为固化的规范可能与形形色色的现实之事不太合拍,而利作为基础性的寻求我与事之间恰切关联的期待,则一直促使人的生活保持着朝向“合宜”的活力。《系辞传》将之概括为“变而通之以尽利”,道出了历史中如伏羲制人道、神农教稼穑等重大变革的基本意义。 这些变通之举,无一脱离因人心之旁通于他人之情、他人之欲而自然产生的“与天下共遂其生”的意愿;对变通,尤其是其背后的意愿的审视和思考,则可以向我们揭示人性的善,这就是孟子指出“于故之中知其利”以为理解人性之道的原因所在。张丽珠指出,焦循的义理可被概括为“能知故善”,他将儒家道德学说的重心,从“智性”扩展到对“趋利变通”的强调上,(13)可谓的当。 在厘清了上述关系后,焦循大胆断言,“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变不足以言事”,在对利缺乏深入理解的前提下去考察人类历史,只能获得一些偏颇空洞的论断,而在根本上错失孔、孟所传承的“伏羲神农文王周公之道”,即以通变精神贯彻于一切人的活动而求其时时合宜的人道。在对“通变”有着恰切理解的历史观照中,事才真正成为关联着人性的已然呈现与一再被理解的“事”,利、义、宜也由此弥合了概念间的裂痕而在学者的思想中获得一种源于人性本然朝向的融合性的理解。 总而言之,利、义、宜所代表的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统合于能使人性得以自我彰明的“智”中,为各个时代不离于日用常行的人道奠定了基础。至此,焦循完全扭转了“利”在《孟子》义利之辨语境下的消极含义,使之成为与欲、情、知密切关联而又饱含民本思想色彩的一个概念。 不过,孟子在“故者以利为本”的论断下,马上批评道:“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智的穿凿运用显然对人性论迷雾的出现负有主要责任。如何扭转“智”的不利地位,再次成为焦循注疏中的一个重点。焦循的解释思路,是将用智、养性与圣人通变的历史演进过程结合起来,以此来展开他以“旁通”为标志的思想。 四、“旁通”的思想 焦循认为,孟子的“性善”学说不是一人的独创,而是“融会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 《孟子》“性善”之说,全本于孔子之赞《易》。伏羲画卦,观象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俾天下万世无论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赞之则云:“利贞者,性情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禽兽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贞,故不可以为善。情不可以为善,此性所以不善。(《孟子正义》,第755页) “人道”的创设始于伏羲画卦观象,凝结为诸圣相传的“性善”之论,而落脚于区分人禽性情的“旁通”之旨。伏羲之后,人性善的显明与人伦道德的创设成为一体两面之事,神农、尧、舜诸圣的治理天下,是对《易》中“旁通”之义的恰切理解和灵活践行;而文王系辞与孔子作“十翼”,则是希望用文字向后人指明六十四卦所蕴含的“旁通”大义,使之不误(14)。然而,如孟子所说,往往有穿凿用智者淆乱性善之义,使之不能显明。对此,焦循根据“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孟子·离娄下》),指出“穿凿”的真正含义: 《说文》金部云:“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传》云“公凿行也”,注云:“凿犹更造之意。”故赵氏以穿释凿,又以改释之。改即更造也。赵氏以养物言,言当顺其情性以养之,不可戾其情性以养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移,谓变通也。禽兽无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与人异。则人无论贤愚皆能知,即皆能转移,愚者可以转而善,智者可以转而为不善,此习所以相远。智者何以转而为不善,为其凿也。惟其因智而凿,故恶其智。盖伏羲以前人苦于不知,则恶其愚;黄帝尧舜以后人不苦于不知,正苦于知而凿其知,则圣人转恶其智,故无为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孟子正义》,第586页) 焦循训凿为改,将智者之凿解释为改戾人之性情。人的性情即心知是可以变通移易的,孔子所说的“习相远”就强调了后天教化对人性的改变。至于“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特别是不可进于善的下愚之人,根据《孟子字义疏证》中的论述也是可以移易的:“生而下愚,其人难与言礼义,由自绝于学,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怀惠,一旦触于所畏所怀之人,启其心而憬然觉悟,往往有之。苟悔而从善,则非下愚矣。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以不移定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同上,第741页) 因此,伏羲创设人道的目的,是使天下之人,尤其是中人、下愚皆得顺其性而养之,改移积习中的不明、不善,成其可以为善的本性;智者的穿凿与之相反,乃因过度用智反落于不明、不善。焦循借此解释了“上智”是否能移易其性的问题,并指出伏羲创设人道时针对的是民众普遍的愚而不知,故人道的目的在通其心知之明,开显性善之道以化成仁义。 黄帝尧舜以后民智渐开,巧伪奸诈流行不已,智的穿凿违戾了心之知觉发用过程中感通他人的自然趋势,淆乱了自明的条理,使得仁义反而成为外在于心知的空洞言辞。这正是后起之圣转而“无为”的原因。当人的心知以扩充为其主要活动时,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滑向过度和穿凿的危险。羲、农与黄帝尧舜的治世之道的差异,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呈现某种基于必然性的演变轨迹,从探求人道的内在动力来看,则反映了“时行”之义的深刻内涵。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疏解“无为而治”和“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的含义,以进一步发掘焦循思想的主要特征。在“滕文公为世子”章,焦循结合《易》与孔子之言,认为:“盖尧舜以变通神化治天下,不执一而执两端,用中于民,实为万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删《书》首唐虞,而赞《易》特以通变神化,详著于尧舜。”(同上,第318页)《易》的通变精神落实于人类社会,正是孔子所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之道,亦是孟子所说的执中行权、不偏滞于一端。舜作为通变执中的代表,最要在能够“舍己从人”: 其两端,人之两端也。执两而用中,则非执一而无权。执一无权,则与人异;执两用中,则与人同。执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从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从,故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正义》,第241页) 焦循将两端解释为人群中居于一端、具有代表性的各类意见,“执两而用中”指广泛听取多方意见而折衷之,折衷的目的是随时变化、应时之用。统治者居于群众之上,其心常常是“执一无权”的,表现为守己而不能舍己、以己之一心为天下的中心而欲天下人时时从之。舜能够执两用中,正表明他不以己心为天下人之心,而是以天下人之心为己心,惟善是从,且乐人之有善。在《雕菰楼集》卷九《一以贯之解》中,焦循更明确申述此义: 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惟其不齐,则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执己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例诸天下之所习所学、所知所能,故有圣人所不知而人知之,圣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圣人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于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5) 在这里,圣人不仅不是全知全能,反而因众人的知能而使自身知能得到拓展;圣人的“尽人物之性”,恰恰是通过自觉己性并非全知全能而自虚其知、自抑其能,而为他人尽其知能打开空间。这一说法大有道家“无为而治”的意味。对此,焦循联系《论语·为政》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材料,指出: 盖尧舜之“无为”,正尧舜之“用心”。曰“为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修己以敬”,曰“使民不倦”,曰“使民宜之”,非用心,何以为德?何以为恭为敬?何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故尧舜治天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政逸而心以运之则劳,其法疏而心以联之则密,非运以心,联以心,不能“无为而治”,即不能“民无能名”。 尧舜的“用中”表面上是虚己之心,实则在深层意义上仍是心之知觉的发动。心具有向他人感通的本性,以己之性情例诸天下性情是这一本性的浅层发动,而舍己从人、惟善是从所朝向的更加协调良善的人际关联和人的存在状态则是这一本性更为深层的展开。正因如此,尧舜那看似闲逸疏阔的治理措施,才因心的运之劳、联之密而既不落于法条繁琐的窠臼,又不致走向脱离文明的蒙昧。 心在治理活动中为寻求民众的“得宜”“利贞”所进行的运转联通,因其合乎人性的本来要求而特别成为统治者所应该依循的道德导向。焦循此说吸收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合理因素,并将之消化转变为儒家思想传统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不仅扩展了儒家思想的深度,在清代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至于“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焦循借“行之而不著”章讨论道: 行、习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圣人知人性之善,而尽其心以教之,岂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则以行而能著、习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习而不察者,众庶也。则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庶也。众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尽其心,通其变,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虽分而义实相承,玩之可见。 《易·上系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日用而不知,即所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众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阴一阳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由,惟其能由,所以尽其心。以先觉觉之,其不可知者,通变神化而使由之。尽其心,显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诸用也。圣人定人道,虽凡夫无不各以夫妻父子为日用之常,日由于道之中,而不知其为道也,此圣人知天立命之学也。圣人知民不可使知,则但使之行、习,而不必责以著、察。说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责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孟子正义》,第884-885页) 人性既有上智下愚的区别,则穷极天道人性而为人道奠基的高明之思,只能属于少数天赋聪慧且善用其智的君子;使所有人对天道和人性发生根本的照察和理解,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对以先觉自任的君子而言,大多数民众窘于生计、昧于人伦的现实遭遇促使他们必须把行、习、日用置于著、察之前。而欲使民众行之、习之、终身由之而不倦于人伦之道,亦非易事。尧、舜对羲、农以来的人道进行变通,后王又一再变通之,表明作为一套固定下来的规范的人道是无法长久而灵活地跟随时势推移的;不能应变,则规范之用渐至于困穷而为人心所厌倦,进而失去其与人心知觉感通之能的内在联系而流为浮文。 一代代圣贤不断变通而使人道得以损益更新,运之于民而使之不倦;民众的日用不倦不是基于对天道人伦的高明理解,而是根源于天道流行所赋予的气血心知的自然运行与人道的内在关联。或者说,原本显见的、规范化的人道因与时移易而与不被概念化所穷尽的人性得以保持内在一致,对这种一致的保持奠定了人道可以贯通运用于一切人的生活而不受阻碍的基础,这恰恰是责民以著、察的抽象的理论宣讲所难以达到的。因此,“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不仅不是所谓的愚民政策,还非常符合人道运行与民众生活的实际。 焦循的“通变”学说推重历史中的圣贤之用。在他看来,圣贤与常人之别主要不在性的差异,而在对“命”的理解。孟子的性、命之辨,已经暗含了圣凡之别,焦循更明确揭出君子之于“命”的责任: 正义曰:天道,即元亨利贞之天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义礼知之常,此圣人之于天道也。乃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谓“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赵氏谓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口鼻耳目之欲不遂,属之命;而仁义礼智之德不育,亦属之命。 然颛愚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劳来匡直者有以辅翼之,固限于命矣。若君子处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则任之于命而不事外求;其仁义礼智之德,则率乎吾性之所有而自修之,不委诸教化之无人,而甘同于颛愚之民,所谓“虽无文王犹兴”也。 且由是推之,父顽母嚚,命也。而舜则大孝烝烝,瞽瞍厎豫,此仁之于父子,君子不谓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则勤劳王家,冲人感悟,此义之于君臣,君子不谓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则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蓧之洁身,而明道于万世,此圣人于天道,君子不谓命也。《大戴记·千乘篇》云:“以为无命,不偷。”以为无命,即是不谓命。(《孟子正义》,第993页) 在一阴一阳流行不息、元亨利贞日成而日新的天道变化中,人的口鼻耳目之欲与仁义礼智之常统体源于气化禀赋而并谓之命,此得于天道的禀赋在人之一身呈现为欲、情、知的心知结构,又使得命的内容被谓之为性。这是戴震、焦循及其同时代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而圣凡之别,只在心知之觉与不觉、旁通与不旁通、能推与不能推之一线间。“颛愚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劳来匡直者有以辅翼之”,则欲张其口鼻耳目之欲、明其仁义礼智之性而皆不得不限于外在时遇所造之“命”,且往往为其所驱迫,难以遂欲而成性。 以尧、舜、周、孔为代表的诸圣贤则通其心知之神明,以仁义礼智天道的命为本有之性,不甘于受外在时遇的局限而欲运其知能冲破消极的“命”,成立为之在己的“性”,由尽己之性以至于创通人道、尽人之性,使“颛愚之民”各遂其四体之欲而各成其仁义之性,是所谓“圣人不忍天下之危,包容涵畜,为天下造命”(同上,第112-113页)。 圣贤以造命为己任,能造命者才可当圣贤之名;而多数民众则只能顺命、被动承受命运阻碍驱迫之苦,惟以圣贤造命而达之天下为其扭转被动的、偏离人性本然之状的生存命运。因此,圣贤的造命包含着极为重大的伦理责任,是身居高位、兼有多种优势条件的统治者所理应效法的准则。 “旁通”是焦循《孟子正义》探讨人性论、人道起源与思想的中心点。如其所述,能旁通于他人、开通于仁义的心知是人独一无二的本性所在,这一本性在人的现实生存中展开为欲、情、知的结构,又因“变而通之以尽利”的人的基本生存趋向而统合为一个与时变化的整体。 人性如是呈现的基本结构及其发用特点,使得人道必然通过学以养性、习以成性的过程将人性中的善端推扩为现实的仁义。而人道创设、变通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儒家传统中的圣贤执中行权、应时行义的历史。焦循从心性论、教化论和历史演进论的角度,为统治者所应当遵循的儒家伦理提供了一套全面而立体的论述。这些饱含思辨意味和道德关切的论述,在清代有着强烈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今人亦具有深刻的启发。 注释: ①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②对戴震言义理三书的成书时间考证,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8-368页。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第386页。 ④此句为焦循解释赵歧为《孟子》作章句的特点,亦可以说明焦氏《正义》的著述特点。[(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页。] ⑤(清)戴震撰,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绪言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6页。 ⑥(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751页。 ⑦对“义”包含的“时行”之义的解释,参见林忠军、张沛、赵中国等:《清代易学史》(下),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576-578页。 ⑧(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761页。此为焦循转引《孟子字义疏证》的内容。 ⑨(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753页。 ⑩吴根友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827页。 (11)(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754页。 (12)具体论述参见林忠军、张沛、赵中国等:《清代易学史》(下),第574-582页。 (13)张丽珠:《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台北:里仁书局,2003年,第209-210页。 (14)参见林忠军、张沛、赵中国等:《清代易学史》(下),第531-532页。 (15)(清)焦循著,陈居渊主编:《雕菰楼文学七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09-210页。 作者:王沁凌,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