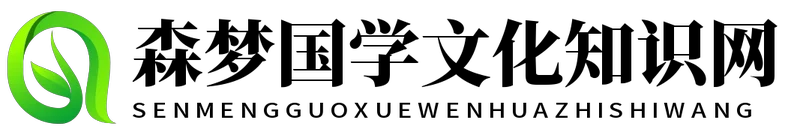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中庸”是中国传统的核心理念。孔子是“中庸”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中庸》篇则是最早专门论述“中庸”理念的儒学经典。后世理解“中庸”思想和“中庸”价值,《论语》及《礼记·中庸》篇无疑是最为便捷的门径。今天的《中庸》诠释路径中,“心性——超越性价值”一维更为多数人所熟悉。然而,细证“中庸”思想的源头与脉络会发现,“中庸”思想内在结构具有双重性,不仅有“心性——超越性价值”的一维,同样还包含着规范性价值的维度。在孔子处,中庸的“双重维度”并未构成理解上的冲突,这两重维度之间还具有内在秩序,“规范性价值”必然附着于“心性——超越性价值”而存在。在后世的诠释中,汉儒更偏重其规范性价值的一维。从源头来看,“中庸”思想具有多重性。从根本上讲,“中庸”指向“无过与不及”的恰好处,推致其极则必然至于形而上之境而不落于经验实存。如将之施行于现实之中,它必然表现为一种规范。这种规范一方面是理想人格样态,另一方面则是具体的社会规范。理解“中庸”思想必须要注意其内在的多重性。 作为社会规范的“中庸”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而《论语·尧曰》篇则记载尧对“中庸”的称述,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两处对“中”的称赞实际上都预设了中的规范价值。民应该长久的按照中庸之德生活,而舜则需要“执中”以使天下永续。汉代儒者将“中庸”的这种意蕴发挥到极致。“中庸”“中和”在汉代都关系到两大问题,即圣人问题与礼法问题。圣人是儒家崇尚的理想人格。如何理解圣人关系到礼法,也关系到作为教化核心的“五经”。当然这并不是汉儒的独创,先秦儒者已发其端,《荀子·儒效》言:“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孔子之语曰:“夫礼所以制中也”。郑玄对“中”的理解显然受到了这些记载的影响,他言“惟礼能为之中”,正是“礼所以制中”的另一种表述。以“礼”作为“中庸”的关键要义并不意味着“中庸”只能是经验形态,它仍然需要礼的践行者在礼制的具体实践中体会其背后的价值深意,并自觉地“导己归中”,复正情性。其极致也同样是非经验性的境界。不过,总体而言,汉儒对“圣人”以及“中庸”的理解呈现出浓厚的社会规范色彩。这与先秦儒家有些许的差别,当然,这也与汉儒对时代的独特理解息息相关。 夫子言“政者,正也”,这是积极理解社会规范的典范。儒者的社会理想寄托了更高的价值追求,“为政以德”以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无不是这种追求的体现。因为,民并不是完整意义的主体,其需要从“暝”的状态走向“明”。儒者所肩负的任务就不是对所有主体的管理,而是如何导暝归明。汉代儒者将君子看作德性的维护者与推行者,这与汉代的人息相关,尤其是董仲舒的“人性论”对汉代儒者的巨大影响。他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自身不足向善,它留待礼乐的教化。这也就为社会规范的推广划出了空间,然而,礼乐政教的来源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源自“察乎天地”的圣人。因而,推广社会规范的关键点就落在圣人问题上。自然,这是两汉儒者在特殊环境下的论断,这些论断与先秦的儒者则已经有些许差异。 在两汉儒者看来,子思作《中庸》的目的是“述祖德”,就是赞述作为圣人的孔子之德。中庸既是一种性情之正,又是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的状态。这种状态常人难以企及,唯圣人能合于中庸。但在东汉大儒郑玄理解中,作为生而至诚的圣人所具有的中庸之德正是他必然制作礼乐的内在原因。因此,“中庸”是内圣外王的综合。不过,郑玄强调的是圣人的外在规范。这与整个汉儒对的理解分不开,如同董仲舒将政教看作“成性”的决定因素,郑玄也将“政”看作一种必然。在“哀公问政”章中,孔子言“人道敏政,地道敏树”,郑玄注之曰:“敏,犹勉也。树,谓殖草木也。人之无政,若地无草木矣。敏或为谋。”土地必须生出草木植被,否则就是废地,而人则必须要有政,否则不成其为人。“人道敏政”昭示着儒家式的人本属性,敏不管作“勉”还是作“谋”解都意味着社会生活是人的根本处境,这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判断类似。更重要的是,为政者借用布于方策的文、武之政来养育、教化百姓。郑玄认为“夫政者,蒲卢也”的蒲卢乃是蜾蠃(土蜂),它取桑虫之子以为己子而养育之。“政”就是上位者如同蜾蠃养桑虫般养育百姓。既然社会生活是人的根本处境,那么好的社会规范就应该成为目标,而最好的规范无疑来自最好的人——圣人。 从圣人到社会规范 古希腊的柏拉图声称“知识即美德”,真正的德性依靠主体对真正知识的理解和深化,只有在人的德性践履中,知识方可转化为真知。正如《中庸》篇所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不管是仁还是智都是上天赋予人之本性的自然功能,这些自然功能表现为一种潜能,需要人自己去实现它。在根本上,中庸之道在人间事务中的实现依赖于人本身,中庸之道虽能成全人之为人,然而夫子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中庸之道始终意味着修道之人在成全自身,使自身获得更高的境界。而在现实中,作为理念的中庸之道往往难以成为人们行事的严格准则。因为,能够将中庸之道见之于自身的践履需要主体对自身所禀赋的人之为人的向善天性具有相当的把握,同时,他又须对森然万殊的自然万物与纷杂的人类事务具有充分地了解。众人践履中庸之道的过程中有了最好的助力,那就是在中庸之道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人。如以其自身的视角来看,他们绝不会自认为已达极致,总是留有提升的空间。但众人却将他们都看作了“圣人”,认为他们可以作为个人自身德行修养的范本,他们通过对中庸之道的践履所形成的价值原则还能为众人的生活提供规则与秩序,使得众人皆有向善的通道。圣人与中庸之道变成具有同等价值的存在,作为人道之极则的圣人更能亲切而显明地向众人展现难以把捉的中庸之道。孟子在《尽心下》中对此有着更为确切的表述,他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善、信、美、大、圣、神乃是一个向上价值的序列,中庸之道与“圣”的精神实质都是要为人持续提供一种向上的通道。孟子甚至在圣之上更加上了“神”的维度,这绝非神秘的宗教语言,他意在表明就算是达到“圣”的境界也仍然有提升的可能。如果封闭了这种形而上的可能性,这种学说无疑会变得凝滞而盲信。 如果以理念为标准来寻找作为标准和规则制定者的圣人殊为困难,就像在现实中找一个完全恰到好处的一度一样困难,或者说根本不能完成。因此,“中庸”的理想人格往往下降到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物身上。从一开始,圣人并不如后世经孔子润泽后的观念那样。他们集中体现了先民的生命意识,他们或为沟通天地神祇的巫觋,或为制作器物的智者,或为开创王朝的统治者。以其行迹而言,他们都在汲汲于解决生民之命的问题。如果以后世圣人观念的视角来看,这些人皆有所不足,如孔子后学所言:“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然而,如果以人文化成的视角来看,这些上古圣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华夏之民趋向更为文明的生活。孔子虽未曾明言这些上古杰出的人物就是圣人,但也对其多有赞誉。孔子意识到了理想人格须“由仁而圣”,须“博施济众”。这两种意蕴并非割裂的两截,实为一体两面而已。孔子以其自身的行迹以及他的制作为天下万民以及后世指明了朝向更高价值的一种可能路径。 作者:谌祥勇,重庆市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