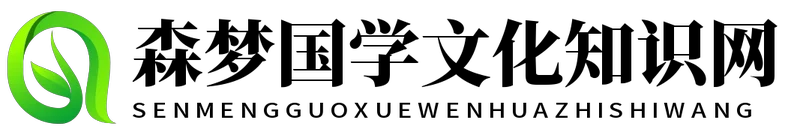孟子的“性善论”长期以来被误解,说这是“人治”的理论基础,所以中国文化无法发展出“法治”,而信教“原罪”和“性恶论”的“西方”,不相信人性可靠,所以发展出用法律约束人性恶的“法治社会”。《孟子·告子上》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以及《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些经过“现代启蒙”的读者看了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人性的善怎么会是向水往低处流这种物理现象一样?而且“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性善成了天然而然的本性,还不是外部教育和输入的结果,实在荒谬。所以一些“启蒙”后读者会说,中国文化没“幽暗意识”,盲目相信人性善,不防备人性恶,所以走向了“人治社会”。 但问题是,最讲人性恶的韩非子,是不是就引导大秦朝走向了“法治社会”?毕竟韩非对“人性恶”的观察达到了极限,《六反》篇中说父母和儿女之间也只是互相算计利害,《备内》篇中说嫡子和后妃都盼着君父早死,至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之间,那更是互相算计谋害;而普通平民之间,则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也是互相争斗互害的画面,讲的是最赤裸裸的人性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彻底的冰冷算计和互害,比非洲草原上的野兽还凶猛。那么既然人性如此丑恶,要维持秩序当然只能靠君王的法、术、势权柄,再加上石壕吏的皮鞭,才能驯服这群互害野兽。在韩非子的人性恶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是互害的原子个体,连父母和子女之间都不靠不住的,那么这种世界怎么可能存在比较善意的自治小共同体?甚至韩非本人也死于自己的同学李斯之手,而不是和李斯同学之间建立起一个互助的同学会共同体。可以说,性恶论并不会推导出“法治社会”,反而可能是有助于彻底瓦解一切共同体束缚和伦理底线的思想。 还有很多现代人,似乎更能接受告子的观点,即“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说人性的善恶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已,其实无所谓善恶,主要靠后天的教化。关于告子的学派,郭沫若认为属于“黄老”,和宋钘、尹文属于一类(《十批判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陈来则说“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往往使人忽视了告子也是一个儒家”(《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91页)。告子一类的人性论观点,也见于郭店楚简儒书《性自命出》“其用心各异,教使之然也”,“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就是说善与不善其实更多是形势所塑造的。如陈苏镇所论,“此说显然是‘性有善恶论’”(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与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143页)。结合这些来看,告子应该属于不同于思孟学派的另一支儒家。在很多现代人看来,告子这种思想至少比孟子的性善论靠谱:人性都差不多,主要是后天环境,尤其是“原生家庭”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当然,现代人有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幼年心灵创伤等一系列关于“后天环境”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有其社会价值。但是如果基于这些,就将孟子的性善论视为一种幼稚的认知,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孟子为人性善辩护,其实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战国时期编户齐民制度的普遍确立,逐渐瓦解了早期基层社会中自治能力比较高的村社、宗族等小共同体,人们成为官府乡、里基层组织控制下的原子散沙,实行连坐和鼓励告发,进一步激发了人性中恶的元素。东方齐、魏等国虽然没有搞到秦国商鞅变法后那么严酷,但也都通过这套弱民术强化了政府的汲取能力和军国动员能力,魏国的《户律》《奔命律》要严厉打击商人、赘婿之类,不给他们分与土地房屋,甚至将这些贱民直接拉到前线当炮灰填沟壑,这些残酷的军国动员手段,也得到了秦国官吏的欣赏,因此将其抄录在云梦秦简牍中。可以看到,魏国在内的三晋,既是法家思想的起源地,其变法后的制度政策,很多又和“暴秦”能够汇通。魏国的梁惠王对孟子说他东败于齐,长子死焉,仅就这一场马陵之战,魏国就死掉了十万武卒,可见其国家动员强度之高,而背后对应的,正是残酷的资源汲取过程。我们后来熟悉的《石壕吏》一类基层动员和汲取的画面,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人性是凶恶的,而不是善的。那么孟子针锋相对,专门大讲人性善,一定和他对基层社会组织的辩护、诉求方式是相互配合的。 孟子诉求中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实现西周时期以村社、家族等民众自治小共同体为基础的井田制。后人对井田制误解极大,以为是豆腐块形状的“土地国有”,笔者曾在《孟子与三代时期的小共同体治理》(《孔子研究》2020年1期)中指出,井田既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而是一种类似西欧封建时代的土地保有关系,所谓“公田”按照瞿同祖的分析是“和英国封建社会所谓公田(Lord's demesne)相仿佛”(瞿同祖:《中国封建 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3页),通过封建效忠和保有的方式,土地从周王一层一层被保有到基层的自治村社,西周铜器《季姬方尊》中,记载基层组织是“厥友廿又五家”,“友”在周代指有血缘关系的族人,因此这是一个以家族组织为纽带的村社。这些基层村社,不是战国秦汉那种“皇权下县”以后乡、里管辖下的编户齐民,而是有自组织能力的小共同体,其中绝大多数以血亲关系为共同体纽带。 《孟子·滕文公上》描述这种自治小共同体的面貌是“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他们有血缘或模拟血缘的亲密关系“友”,在日常生活中高度互助,井田的共同耕作与收获也是这种互助的重要部分,在遭遇疾病或灾害的时候,小共同体成员之间是互相援助,而不是像编户齐民那样互害。这种小共同体互助的画面,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诗经·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描述周代基层村社中,秋收以后会在田中留下一些谷穗,给没有壮劳力的寡妇,很典型是小共同体的内部互助,这是养成我们一般人熟悉“善”这种概念最适宜的场所和平台。 我们智人这个物种确实有凶残的一面,但智人的基因与心智相伴随演化了二十万年,这二十万年的漫长演化过程中,其实通过优胜劣汰绑定的基因类型是最适应在“邓巴数”(Dunbar's number)规模范围内的一个小群体内的,即维系在一百五十人规模左右的部落圈子内。在最大邓巴数这个范围内还能拼命作恶的基因,其实大多是被淘汰掉了。在这个小共同体内,智人的大脑可以有效维持紧密的友谊、关系与合作,并形成“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机制。 对于这个一百五十人规模共同体以外的其他人群,智人可能会表现出凶残和攻击性,但在这个群体内部,则讲究各种善意,这是漫长二十万年演化和基因选择的结果,倾向于在邓巴数范围内互害的部落群体,基因更难传递下来。梁山强盗杀人如麻,但却要在一百零八人内部讲究结拜为兄弟,讲究“义”这一规矩,一百零八人正好在“邓巴数”范围内,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攻击“部落”以外群体的古老心理,在现代社会可以被调动起来进行侵略,也可以动员用于保家卫国,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和镌刻在基因中的本能。由于超出邓巴数范围以上,由成千上万人组成更复杂群体进行合作的文明史,只有区区五千年历史,智人的大脑还来不及进化并适应规模这么大的社会组织与协作模式。只有一些极少数天才的大脑,才能处理高度复杂流动、陌生人社会合作社会的庞大信息,如南朝的王弘可以“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南史·王僧孺传》),每天处理远超过邓巴数以外陌生人的大量信息,而且不触犯他们父亲、祖父的名讳,那么处理的人物信息量就更加惊人;梁、陈时期的大军阀王琳,能够“强记内敏,军府佐吏千数,皆识其姓名”(《南史·王琳传》),以一个低贱兵户出身没文化的人,却能记住自己下属佐吏上千人的名字,也是天赋能力了;北齐的唐邕,据说也可以“于御前简阅,虽三五千人,邕多不执文薄,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谬误”(《北齐书·唐邕传》)。唐朝的李敬玄,“性强记,虽官万员,遇诸道,未尝忘姓氏”(《新唐书·李敬玄传》),能记住上万人的姓氏。另外唐代的唐宣宗也特别能记住大量陌生人的名字和信息,所谓“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九年),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仆人的姓名与特长,都能熟记于心,且能记下唐帝国众多狱吏卒的名字。此外,古罗马的凯撒,据说也能记下自己的手下每个士兵的面孔和名字。显然,王弘、王琳、唐邕、李敬玄、唐宣宗、凯撒这种能处理远远超出智人部落本能信息的大脑,毕竟只是少数,因此才上了史书,被大书特书作为佳话。而一般普通人的大脑能力,其实和旧石器时代晚期差异并不太大,更常见的情况就是“脸盲”,即不能识别超过自己熟悉最大邓巴数圈子以外的人脸和信息。毕竟,大脑与复杂社会组织协同演化的历史才五千年,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心智情感,仍然是高度基于并依赖于更古老的智人二十万年以来的小共同体结构,或者其各类变体的。 孟子敏锐地观察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种小共同体是“善”最重要的载体或蕴蓄形式,强调性善论的另一面,其实就是要利用好智人“部落心智”的这种古老本能,才可能为成千上万人更复杂的文明体量合作来服务,并且规避可能遇到陌生人更容易互害的短板。 人性是高度复杂的,孔子和七十子后学基本不讨论人性的善恶问题,这是因为空谈人性善恶,很容易成为无意义的抽象玄学。善和恶,一定要放到一个共同体结构或语境中才是有意义的。在共同体内杀人,这是罪恶。但如果杀的是共同体之外的日本侵略者,这又成为本共同体的一种善。在孔子、七十子们百年后生活的孟子,正面对最后的基层小共同体自治遗产处于崩坏和解体的前夜,编户齐民和更高动员能力的军国组织已经呼之欲出。在此背景下,孟子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甚至重建西周的“井田”,其实就是要保留“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自治小共同体,给社会基层留下一口元气。那么人性善的学说,恰恰与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相匹配,因为人生活在熟人社会,尤其是有自治能力的社区,人们之间的博弈时间线条非常的长,很可能是很多代的之间祖祖辈辈世代打交道,那么这种社会结构中作恶的成本就非常高,作恶被摈斥出共同体后丧失共同体的保护,这是非常不划算的,因此小共同体内部人们普遍更加行善,是培育“善”的重要蕴蓄形式。反之,韩非子式的性恶论讲父母和儿女之间都互相为恶,那么这种社会根本不可能妄想什么自治小共同体,石壕吏的皮鞭管束就是其必然命运。 如果人性恶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就像霍布斯笔下那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那么最好的结局一定就是无所不管的利维坦。如霍布斯所说“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在这种以人性恶为预设的状态下,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武器,就寝时要紧闭房门,就算在屋子内,也要将箱子锁上。([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4-95页)这种人与人之间全然处于性恶论所预设的战争状态,最终当然只能依靠“利维坦”来提供救赎与秩序。但是从历史经验和发生学的角度而言, “利维坦”诞生之前并非如此。即使是史前时代的人们,也是生活在各种家族、氏族、部落等小共同体之中的。在当时,不同族群之间确实存在着残酷的“战争状态”,却并不存在“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这种状态。换言之,在家族、部落等小共同体内部,凝聚起人们的力量并不是人性恶,而是人性善。霍布斯也观察到,“美洲有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除开小家族以外并无其 他政府,而小家族中的协调则又完全取决于自然”([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第95页)。他其实也意识到,即使是在最“野蛮”的状态下,也有小共同体的存在。可是霍布斯却认为小共同体的内部,是按照“自然”来进行弱肉强食的。然而实际是,按照“自然”搞下去,小共同体会迅速瓦解。在小共同体对抗小共同体的史前时代,只有内部更加“亲爱精诚”的小共同体,才更加具有对外的竞争力。这种远古时代小共同体中对性善的培育,能够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早在荒蛮古老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供养丧失了生存能力的伙伴与老人了。例如,沙尼达尔(Shanidar)遗址中曾发现一名大约40岁的男性尼安德特人,其左眼部分失明,右臂自小就萎缩无用,脚趾骨上有裂缝,膝盖和髁部有关节炎。考古学家指出,如果没有别人对他的帮助和供养,像这种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英]科林·伦福儒、[美]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一个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废人,依靠小共同体的保护,居然能够活到史前时代的高寿年龄。这说明即使是在资源极其有限的远古荒蛮时代,小共同体也依然尽力保护内部的弱者与老人,而不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小共同体是培育人们理解“善”知识的最早、最古老的培养皿,有着长达数十万年的历史,伴随 着整个智人物种的演化。“善”的知识与经验,以及性善的实践,与小共同体的关系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在传统小共同体逐渐解体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并不是一种“傻白甜”行为,恰恰相反,这是在论述人民有互相行善和自治的能力,不需要官府用鞭子管着。只有搞好了最大邓巴数范围内小共同体的善,在其中训练、养成善和放大善的种子,才有机会将这种善进一步扩大到大共同体和陌生人,或者以“同心圆结构”的方式,一层层向外辐射善意,当然越内核越是浓密,越外层越稀少,更远和更陌生的群体之间能通过贸易往来做生意形成合作就行了。最内核的小共同体,当然就是家庭,是孕育“善”的最初起点。当然,很多人也可以从经验角度找到很多反例,指出家庭存在着“恶”的一面,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吴虞等人以来从来不缺少这类控诉。但是这无法解释,即使是陌生人之间要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也首先会通过模拟家庭的称谓来实现其关系建构,而不是相反。如果家庭是万恶之源,那么恰恰应该相反,家人之间应该互称“我们是陌生人”,以表达善意,才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是从人类学的视野来看,最常见的,恰恰是陌生人之间会通过模拟家庭来表达善意。如拜把子互相称“兄弟”,把领导称“义父”,把一些比喻为“母亲”,甚至“朋友”一词最初在西周金文中也是指有血缘的兄弟或堂兄弟关系(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14页),后来陌生人之间也称“朋友”以拉近关系。人们普遍将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辈男性称为“哥”,女性称为“姐”,更长的称为“叔叔”“姨”这类模拟家庭成员的称谓,会迅速拉近距离并感受到善意。哪怕一个匪徒在喊出“弟兄们”的时候,这一模拟家庭成员的称谓也会迅速拉近其成员的向心力。人们将自己毕业的学校又称“母校”,甚至商业广告也会宣称让你感觉到“回家”或“家的温暖”,而不是宣称“感受到陌生人待遇的温暖”或者“感受到陌生人社会的边界感”。现在网络上为了流量和套近乎,都将陌生人称为“家人们”“兄弟们”,也是典型的通过模拟家庭成员关系,来拉近善意。这种陌生人之间以模拟家庭关系实现合作,互相感受到善意,具有极其古老的历史渊源,且广泛见于世界各地,表明家庭这种小共同体,一定是酝酿“善”最初的起源,然后才向外流溢出去的,成为构筑更外围不同圈层,直至陌生共同体的一种资源。 这一古老且普遍的历史现象表明,人类历史文化的绝大多数语境下,仍然是将家庭视为善这一价值的根本来源。可以推断,史前时始,以家庭这一最核心小共同体,是培育善的基石,再外推到氏族,再外推到部落。进入文明时代,则将其向国家、族群甚至“天下”进行外推和外延。孟子强调人性本善,其实就是要立足于小共同体的这一古老智人本能,让大共同体不要突破其应有边界,再以同心圆圈层的方式将善意层层外推,去实行规模体量巨大的复杂社会合作,将小共同体为本位培养出来的善意,一层层向外流溢。如果小共同体得不到保护,那么得到的绝对不是大共同体之间就能获得善,相反,只会得到陌生人之间充满恶意的各种肆虐行为。性善论的潜台词是,人们有组建小共同体,并以小共同体自治来实现治理的能力,而不需要天降石壕吏,得拿着鞭子像防贼一样,用鞭子管着。 本文摘自李竞恒著《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