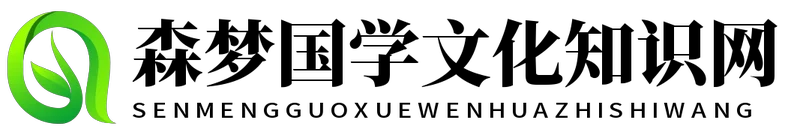子张在《论语·子张》中具体阐发了其老师孔子“尊贤而容众”的教诲。总览文本,孔子的“尊贤”言论主要集中于其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共涉11篇29章,论及的先贤有唐尧、虞舜、后稷、大禹、商汤、武丁、泰伯、虞仲、周文王、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周武王、周公旦、齐桓公、管仲、柳下惠、少连、令尹文子、宁武子等,言语之间表达了对他们的深深敬意。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试图为世人树立效法典范,以期挽救时代颓势。 圣君层面,如盛赞唐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以为当下君主塑造遵从天道的膜拜圣像。这个“天道”,就是孔子自己解释的“政者,正也”(《颜渊》)、“(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以德服人;“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当政者只竭诚为民而绝不为己。具体表现则为“非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自己吃得坏、穿得烂、住得差而全力造福百姓。再如称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靠埋头苦干得天下,进而礼赞泰伯“三以天下让”(《泰伯》),“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季氏》),屡屡主动礼让天下甚至不惜饿死,认为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的典范。其无疑是力图能以这些先贤做榜样,对当时颓风有所警示。孔子同时还以这些先贤“不念旧恶”(《公冶长》)勉励争位者放弃个人恩怨而共谋太平,如此则就会像先贤一样“求仁而得仁”(《述而》)、“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民到于今称之”(《季氏》),最终赢得民众的永久怀念而名垂千古。他还高度认同尧舜的公平公正(《尧曰》)、商汤的代民罪己(《尧曰》)、商王武丁的谨守孝礼(《宪问》)、周武王的任人唯贤和举逸宽下(《尧曰》)等具体执政措施和行为,无不有为当时国君树立样板之意。与之相对应,孔子还树立了个别历史反面形象,如夏代君主羿和奡靠武力逞强而身死名灭(《宪问》),用以警示当政者唯以德立国方能长久。 臣子层面,孔子最为尊崇的是辅佐圣主成就伟业的先贤。这方面他心目中的偶像一是周公旦,一是管仲。孔子曾感叹自己“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他对辅佐周武王统一天下并代少年成王执政而制定典章制度的周公旦崇拜程度可想而知;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将不以武力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置于至高的“仁人”地位。其次是尊崇恪守臣道的先贤。如盛赞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行为“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在对鲁大夫柳下惠“为士师(官),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微子》)的行为深表肯定的同时,斥责“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位)也”(《卫灵公》),为柳下惠的多次被罢免而鸣不平;更将“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的楚相令尹文子视为“忠矣”(《公冶长》)的人格代表。另外,《论语·微子》还记录了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人之名,虽未见孔子评语,但从称其为“周有八士”,便知也当是孔子师徒推崇的先贤。从如上评论不难看出,孔子对当时各国宫廷犯上作乱频发现象充满焦虑,并为阻止乱象而不断树立正面历史典型,以感化时人,将关系转化为了一种伦理自觉,不免体现出其浪漫的理想色彩。当然,孔子推崇恪守臣道并非是主张臣子一味地“愚忠”,他的理想是明君贤臣式的“君臣义合”。他不但认为只有当政者“为政以德”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而且回答鲁定公之问时大胆直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的君臣伦理对偶论。因此,孔子称颂殷纣王时的微子、箕子、比干为“殷有三仁焉”(《微子》),还对宁武子的行为发出了“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的由衷赞叹。如此,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中,又蕴含了“监督”思想萌芽,形成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士人文化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凡涉人物评论,孔子都非常严谨,既反对道听途说,更反对想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道听而涂(途)说,德之弃也”(《阳货》),“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验证)矣”(《卫灵公》),认为评人必经调查研究。尤其对社会一边倒的人物评论,孔子特别警觉,提醒出现此类现象更有必要对其原因作深入考察,所谓“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即是。具体到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虽因孔子“述而不作”致不易见到他的具体研究过程,但作为“信而好古”(《述而》)的历史文化巨人,他既然自信“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比夏商后裔对各自祖朝的历史还清楚,其对每位所评历史人物的相关文献,一定是了如指掌并做了系统研究的。由“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卫灵公》)的自述可证,孔子通过系统研究,确实发现了古文献中不少存疑之处。如将唐尧、虞舜等“传说人物”确定为历史上实有,必是经过了自己去伪存真的辨析与判断;将后世长期争论的是叛国还是弃暗投明的微子定性为仁人,也必定是掌握了更为翔实的“内情”文献。子贡曾转述孔子观点,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张》),更是在对历史深入研究基础上,对后代恶评殷纣王之文献的质疑辨析。因此,孔子评论历史人物的前提依据都是信而有征的。 更为可贵的是,孔子已认识到了人的不完美性和历史局限性,并认为伟大不等于完美。基于这一认知,孔子对历代前贤的评论,并不一味歌颂,而是采用了两分法与整体论的统一,既歌颂其功德,又指出其不足,并整体尊崇。如在歌颂尧舜遵从天道的同时,又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雍也》),不仅质疑尧舜完全自我制约而使全体民众安享美好生活实际上很难真正做到,还认为即便是单单惠济全民一项,也仅可作为美好的理想目标未必能够完全变为现实。这是一种求是精神,并不影响尧舜的伟大和孔子对他们的崇敬。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对管仲的评论。孔子对管仲极为尊崇而称其为“仁人”,但同时又批评他“之器小哉”“焉得俭”“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认为如此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才是一位完整的管仲,这一评论颇具辩证法因素,亦符合人性实际。对作为人物的管仲而言,其尤为严重的人格污点是“认仇作主”。旧主公子纠被齐桓公所杀,管仲不但没有从死,反而转辅杀害旧主的齐桓公,因此常遭时人诟病,就连孔子的学生们也对此不断发问(《宪问》)。而孔子则以“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作答。合并统观《论语》孔子对管仲评论的四章内容,至少发现三点:一则孔子是怀着真诚的礼敬之心评论管仲的;二则“仁人”不等于完人,应“爱而知其恶”(《礼记·曲礼上》),但更要“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看其大节而宽容小疵;三则人物的大节是什么?孔子认为就是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综上可见,“尊贤”思想贯穿于孔子评论历史人物言论始终。既敬古圣先贤之伟大,又知人各有不足,并以“薄责于人”(《卫灵公》)“无求备于人”(《微子》)的包容和良善心态,“乐道人之善”(《季氏》)。这既是孔子心目中“至矣乎”(《雍也》)的最高美德,也是值得今人汲取的孔子智慧。 作者:徐正英,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