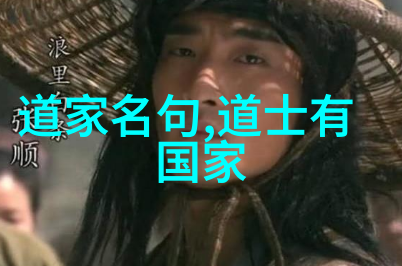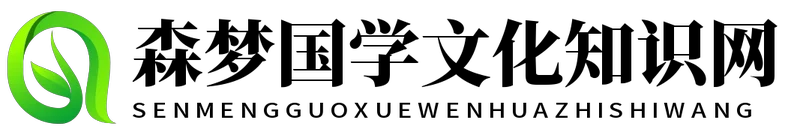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自劝善运动兴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产生了多少道教善书,没人也没法精确地统计。仅据《道藏》与《藏外道书》的收录,它即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经书既可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也可以被视为一套解释系统,还可以被视为一套仪式系统[1]。其对中国后期社会与伦理影响至深,全有赖于此一多性特色。 一、作为伦理系统的道教善书 以兴善去恶为旨归,道教善书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据统计,《太上感应篇》篇共列出善行26条,恶行170条[2]。其中,有34条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而有120条涉及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利他行为。故有学者认为,“处理家庭、社会关系的道德伦理是《感应篇》中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其中包括家人、朋友、为官、经商等等方面的道德原则。”[3]因其如此,日本学者窪德忠不同意将《太上感应篇》视为民众道教经典──“如果把它称为民众道教的圣典,那么民众道教岂不完全等于中国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了吗?”[4]不管怎样,《太上感应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极度关注应是有目共睹的。不止《太上感应篇》,在《文昌帝君阴骘文》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伦理道德的核心位置:全文仅544字,而有关伦理道德的部分竟有378字,涉及了家庭伦理、伦理、社会伦理、宗教伦理与生态伦理几个部分[5]。《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全文649字,涉及伦理道德的部分则有316字,包括了善行36条、恶行46条[6]。《太微仙君功过格》共立功格36条、过律39条,其确立的依据还是伦理道德[7]。他如《文帝孝经》[8]、《文帝延嗣经》[9]、《文帝救劫经》[10]、《文昌帝君蕉窗圣训》[11]、《十戒功过格》[12]等,除了前后序跋,则全部都是伦理道德的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道教善书都把伦理道德视为劝化的主要内容。 自孔孟始,儒家已有一套绵密的伦理说教。佛教东来,也自带着佛陀的戒律规范。异于旧有的伦理系统,道教善书所开启的伦理系统是一圆融三教的系统。概而言之,其忠孝伦常部分主要应是取自儒家,其十善恶业部分主要应是取自佛教,而其齐物畏神部分则主要应是取自道教。 以仁义为最高统摄,儒家伦理之核心是所谓的“五伦”,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君臣关涉伦理,要求君待臣以义礼、臣对君以忠诚;父子、兄弟、夫妻关涉家庭伦理,要求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兄长友善而弟妹恭敬、夫妻和睦而主从有分;朋友关涉社会伦理,要求相互讲求信誉。《太上感应篇》之“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暗侮君亲,慢其先生”、“攻讦宗亲,刚强不仁”、“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等,应该都是化自儒家伦理。《文昌帝君蕉窗圣训》“敦人伦”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兄弟相爱,朋友以信,夫妇相和,尤当各喻以道,各勉以正。”“慎交游”称:“始终不怠,内外如一,贵贱不二,死生不异,尤当功过相规,亲近上士。”则明显是儒家伦理的直接取用。同样,《文昌帝君阴骘文》之“忠主孝亲,敬兄信友”[13],《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之“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邻,别夫妇,教子孙”,也是直接取用的儒家伦理。《关帝忠孝忠义经》借关帝之口称其为经缘由:“视我赤心,听我微言,为子尽孝,为臣尽忠,父慈母爱,兄弟友恭,夫妇倡随,朋友信义,乡邻婢仆,真诚和气。”[14]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忠孝在道教善书中得到了特别的张扬。《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开篇即明确称:“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亏,可立身于天地之间。若不尽忠孝节义等事,身虽在世,其心已死,是谓偷生。”而《文帝孝经》全是对孝的劝化,其《原序》誉之是“集众孝之大成,而创千古之子则”。此外,如《忠诰》[15]、《孝诰》[16]等,都是专讲忠孝的道教善书。 佛教伦理以十善恶业为其基础。所谓十善恶业,《四十二章经》称:“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十善恶业从身、口、意三方面对人的行、言、思给出了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凡杀、盗、淫、两舌、恶骂、妄言、绮语、嫉、恚、痴则为恶,而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嫉、不恚、不痴则为善。其中,意三业也有表述为贪、瞋、痴(邪见)者,内涵实无多大差别,无外乎是将“嫉”之一业归入“瞋”(即“恚”)中,而将“贪”之一业从“痴”中分出。十善恶业只是一个很粗的伦理纲要,故在佛经的具体阐释中常常更被细化。而这之中,身、口六业较为外显而易为人把握,意三业着落于欲、情、智上,把握较难,常被分疏扩充极细[17]。《太上感应篇》所谓“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之区分,即显然是受到了佛教伦理的影响。其“诳诸无识,谤诸同学”、“谗上希旨”、“念怨不休”、“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怨人有失,毁人成功”、“纵暴杀伤”、“破人之家、取其财宝”、“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嗜酒悖乱”、“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亦多化自佛教的十善恶业。《文昌帝君阴骘文》之“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常须隐恶扬善,不可口是心非”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之“戒杀放生”、“恶念不存”、“淫人妻女”、“坏人名节”、“妒人技能”、“唆人争讼”、“宰杀牛犬”、“奸盗邪淫”、“明瞒暗骗,横言曲语”等,也均应是从佛教十善恶业中化来。在《文昌帝君蕉窗圣训》中,其“戒淫行”、“戒意恶”、“戒口过”直接即是取自佛教的十善恶业。其“戒意恶”要人“勿藏险心,勿动妄念,勿记雠不释,勿见利而谋,勿见才而嫉”,其“戒口过”要人“勿谈闺阃,勿讦阴私,勿扬人短,勿设雌黄,勿造歌谣,勿毁圣贤”,皆不难在佛经关于十善恶业的细化中看到。《文帝延嗣经》之核心说教为“十戒”:即戒宰杀、戒窃盗、戒酷取、戒淫污、戒口舌、戒巧诈、戒忍亲、戒弃子、戒焚焰、戒暴性。除酷取、忍亲、弃子、焚焰不敢强言取自佛教伦理,其他大多没有问题。传为孚佑上帝所示的《十戒功过格》,一戒杀、二戒盗、三戒淫、四戒恶口、五戒两舌、六戒绮语、七戒妄语、八戒贪、九戒瞋、十戒痴,每一条目下再立细目若干,分述功过。但很明显,无论是其大条还是细目,皆为佛教十善恶业及其细化的直接吸纳。同样,传为孚佑上帝所示的《警世功过格》,以意、语、行作为区分,分别列出意善56则、语善39则、行善72则、意恶59则、语恶57则、行恶121则,也是对佛教十善恶业的直接吸纳[18]。凡此种种,均见佛教伦理在道教善书的伦理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 道教善书中有一些属于生态伦理的内容,如《太上感应篇》之“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用药杀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等,《文昌帝君阴骘文》之“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等,以及《太微仙君功过格》之爱怜禽兽六畜、虫蚁飞蛾等条目,这些则应是取自道教伦理。因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观念一直在道教伦理中占有突出位置。在此观念中,人并没有特别的权力,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处,至于相互转化。与佛教戒杀的伦理相得益彰,此一道教伦理在善书中几乎被申发到了极致。《十戒功过格》“戒杀”中,天地生灵被区分得非常细微,杀过也因之被标举得极细。而在一篇名为《关圣帝君劝人戒杀放生多立寿诞广生谕文》的善书中,保护生灵竟致是其唯一的内容[19]。除此而外,道教善书中敬畏神灵的部分也多取自道教伦理。如《太上感应篇》之“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左道惑众”、“轻慢先灵”、“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对北恶骂”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之“恨天怨地,骂风呵雨,谤圣毁贤,灭像欺神”、“假立,引诱愚人,诡说,敛物行淫”、“白日诅咒”等,《太微仙君功过格》之“以言指斥毁天尊圣像”、“每遇斋日及诸节令吉辰故不朝真”以及书章念诵错误等,应该都是道教伦理的厚赠。道教为一多神宗教,相信宇宙万物遍布神灵,故其宗教伦理要求人们时时恭敬、事事虔诚。 不仅仅是圆融三教伦理,道教善书所开启的伦理系统还是一个伦理系统。所谓“伦理”,是指此一伦理系统具有极大的伦理包容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套系统包括了家庭伦理、伦理、社会伦理与宗教伦理4个部分[20]。其实不止,如我们上面所揭示的,生态伦理也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此外,如《太上感应篇》之“推多取少”、“减人自益,以恶易好”、“耗人货财”、“败人苗稼”、“苟富而骄,苟免无耻”、“无故剪裁”、“散弃五谷”、“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逸乐过节”、“贪冒于财”、“假借不还,分外营求”、“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文昌帝君阴骘文》之“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之“重粟惜福”、“斗称公平”、“损人利己,肥家润身”、“好尚奢诈,不重勤俭,轻弃五谷”、“大斗小称”等,即均属于经济伦理的范畴。《文帝延嗣经》“戒酷取”、“戒巧诈”通过几个具体事例,要人们勿强民倍课、巧取豪夺,所卷入的还是经济伦理。《文帝救劫经》“日用章”记有一个由富转贫的故事:“杭州王用先家赀百万,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称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祸被刑,家财破散,子孙作丐。”其劝化的指向亦在经济活动之中。《太微仙君功过格》“救济门”称:“以符法针药救重疾一人,为十功;小疾一人,为五功;如受病家贿赂,则无功。治邪一同。凡行治一度,为一功。施药一服,为一功。”其“不仁门”复称:“凡有重疾告治不为拯救者,一人为二过;小疾一人,为一过。治不如法,为一过。不愈,而受贿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修合毒药欲害于人,为十过;害人性命,为百过;害人不死而病,为五十过。”《十戒功过格》“戒杀”称:“医术不精,寒热误施,攻补错用,致伤人命者,亦曰误杀,一人为五十过。若贪其利而故为行险者,为百过。与人争名而故为行险者,亦为百过。若他人调治不错,故说其错,妄为翻案,致误人者,贪名贪利,二俱有之,为二百过。”“精于医术,救一危症,作五十功;重症,作二十功;大症,作十功;轻症,作五功;小症,作二功;极小极轻症,亦作一功。惟受谢者,非功;或浮于所谢,仍可补记。”这些则又属于医学伦理的范畴了。总之,以其广泛的融摄,道教善书所开示的伦理系统几乎指向了世俗生活、世俗职业的方方面面,卷入了法律与道德监管的双重意义。 唐宋之际社会转型对新型伦理产生的吁求,下面将有专说。无论怎样,道教善书所开示的伦理系统,作为一种极具融摄性、性的结果,的确是顺应了此一时代吁求。宋代以降,道教善书普遍被人们视为道德行为的规范。在明清时期的许多《家训》、《通书》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看到道教善书的基本内容。明清以后,道教善书的许多词句成为日常生活的术语、格言。直至于近,这些道教善书仍然极具活力,翻刻注释不断。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其基本理念的深入社会与人心。是故美国学者包筠雅认为:“最好还是认为它们是被普遍接受的‘中国人的’道德标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