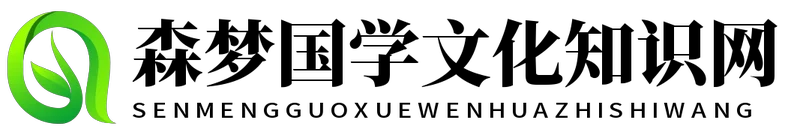一个文明只要有人文经典,就有古典学。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古典学是研究自古以来流传的人文经典的学问,是语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彼此关联的一门交叉性学术。这算得上是东西方古典学的最大可通约性,这一可通约性也不排斥其他的可通约性。由于这种可通约性,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这一词汇虽来自欧洲,但也适用于中华文明。若用中国古老的“经”“典”和“学”这三个字,立一个“经典学”名称,它完全可以同古典学一词互换。 文本的经典化 广义的人文经典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正宗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最有价值的一类著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欧洲,Classics指称的是典范性的著作,Bible或Holy Bible指称的是具有正宗性和神圣的著作(如教、犹太教的圣经等)。在中国,儒家信仰的六经、《汉书·艺文志》所称的“六艺”类书籍、四库全书所称的“经部”书籍都是经典,儒家对六经(或六艺)、十三经的注释类著作也是经典;道家《老子》《庄子》《列子》和《文子》等是经典,对它们的解释性著作也是经典;佛家的经、律是经典,解释经律的论也是经典。若对这两类进行区分,最具原创性、正宗性和典范性和被不断解释的可叫元典,对元典进行解释的子学类著作可叫次典,合称为经典。儒家及其信奉的六经在汉代被体制化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具有了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正统性地位。《汉书·艺文志》单列为“六艺略”,使之不同于诸子略和其他略,《四库全书》单列“经部”使之不同史子集三部就是如此。 文本能够成为经典和被经典化是一些合力的结果。文本的古老性本身就有魅力,文本的创造性使之具有了内在的力量,人们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使之不断焕发出活力,人们对文本中的真理和价值的认同使之具有了权威性和典范性,表彰和规范性的词汇的产生使之从无冕之王成为有冕之王。这一切都发生在早期中国从殷周之变到东周时代的巨大转变中。从东周开始,天系动摇,士阶层纷纷从官学走向私学,诸子各家放言立论。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和编纂的六种文本《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大体确定,并成为他和他的学习的主要书本。《礼记·经解》篇中,“经”就明确被用来指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东周时期将六种书明确叫作“六经”的例子。叫经和六经就是肯定这些书的典范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儒家还将自己的著论叫作经,如帛书《五行》分“经”“说”。 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如道、墨、法等,也有将其著述叫“经”的,道家有《黄帝四经》,墨家有《墨经》,法家也有“经”。汉代以后,儒家因被体制化,经典系统源远流长,从最初的“六经”到“五经”(“乐”失传)再到九经和十三经,“经”的范围不断被扩大;东汉之后中国道教和佛教的诞生,其文本的经典化也不断变化。老子在西汉就被广泛叫经。在唐代,道家的元典《老子》《庄子》《文子》和《列子》被叫作《道德真经》《南华真经》《通玄真经》和《冲虚真经》;慧能的说法被记录下来也被叫作“经”。“佛藏”和“道藏”概念中的“经”都是古典学的中心。新立的“儒藏”体系不言而喻。 诠释的大链条 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断被解释,不需要也不能被夸张到它们都是由诠释者决定的,否则古典学就真的要陷入无公度性的泥淖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文本的经典性永远不能脱离阅读、理解和解释。岂止如此,从东周以来,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叙事、语言文字、文学评说,特别是哲学义理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注释和诠释展开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解释和诠释之链。东周时代同“经”相对的诸如“述”“解”“说”“传”“序”等,都是用来表达解释和诠释“经”的词汇;汉之后使用的“训”“诂”“注”“释”“正义”“疏”“笺”等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解释和诠释链条是何其长又何其复杂。 中国经学史整体上是从六经到十三经的注释史和诠释史。孔子和他的以及孟荀直接注释“六经”的著作不突出。《论语》和《孟子》是语录体,《礼记》特别是《荀子》主要是按照主题展开论说的论述体。《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礼运》等久负盛名,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类文本也是论述体。汉代以后,《论语》和《孟子》重要性被升格。唐代《论语》入经,宋代《孟子》入经。在宋代,《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被单列为“四书”,中国经学也从汉唐以“五经”为中心变成宋代以“四书”为中心。此外道家、佛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诠释史,收入“佛藏”“道藏”和“儒藏”中的著作除了“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则是对“经”的注解和诠释类的著作。这些巨大解释和诠释链条中的著作后来也都成了古典学研究的对象。 诠释方法和形态的多样性 中国古典学,广言之就是中国的古典语言学、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学等。南北朝时期设置的玄、儒、文、史四科,前两者属于义理学,后两者属于文学和历史;明代将学术分为质测、通几和宰理。通几学属于哲学和人文学;清代区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分别相对于哲学、史学和文学。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这是狭义的国学概念,属于广义上的古典学。中国古典学不同领域的划分,也是中国古典学的不同方法和形态。 汉代古典学主要是儒家经学,又有今古文之争,这是儒家内部古典学之争。争论的焦点,一是书写经典的文字和来源不同;二是对孔子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古文同时崇奉周公,认为五经是记载先王典章制度的书,保存了王道的理想;三是今文以“六经”为孔子所作,古文以六经为古代史料和典章制度的汇集;四是今文与古文对经典的诠释方式和方法不同。这些争论主要是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历史学与义理学之间的争论。郑玄合今古文之学而用之,但他的义理学仍弱于训诂学。 与汉唐主要是以五经为主的注疏之学有别,宋代兴起的新儒家既诠释五经,又诠释四书,主要发展的是义理之学;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开始将义理之学往文字学、考证学方向推动,批评义理之学末流的空疏,后发展出清据学,在乾嘉时期达到兴盛。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谓的“汉学”,实指汉代的古文经学,认为清代的考据学、乾嘉之学或者所谓朴学是汉代古文经学的复兴。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批评江藩之说,为宋学和程朱理学辩护,批判汉学。 汉宋之别,义理考据之辨,是经学古典学中两种不同方法的争论,对解释义理文本来说,两者都是需要的;宋学和义理学的解释离不开语文学基础。因此,焦循、阮元等主张汉宋兼容。儒家之外,道家和释家的诠释方法和诠释形态也多种多样。魏晋道家诠释学发展出了玄学;唐代道家诠释学发展出了重玄学。佛家诠释学发展出的学派更多,隋唐佛家宗派兴盛。三教之争并行也好,三教合一也好,都集中表现在信奉、诠释的经典不同及其相互竞争和融合中。 意义和价值信仰 人类是社会性的存在,是按照理性、规范和价值而生活的存在,是靠意义、信念和信仰支撑的存在。除了硬性的强制性规范,伦理规范、意义和价值信仰,理性和智慧,都来自人文经典,特别是来自宗教、伦理和哲学经典及其诠释。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信仰,不仅来自儒家的六经,也来自儒学的经传和论说;不仅来自道家,也来自佛家。按照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儒家主要是正统性的,道、佛主要是非正统性的。 中国古典学,不仅是追求知识,而且是追求智慧;不仅是追求理性,而且是追求价值;不仅是论道理,而且是论道德。道家尊道贵德,儒家求仁求义,佛家信佛信空(悟真悟法),皆为意义和价值追求。东周时代,各家各派就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儒家诠释“六经”其主要表现是将“六经”的意义符号化。 儒家古典学是天人统一之学,是伦理本位学,、成物和成就天下之学,是价值和意义信仰之学。《汉书·艺文志》谓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韩诗外传》强调儒家的价值信仰说:“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谨守,日切磋而不舍也。”儒家信奉的普遍价值“仁、义、礼、智、信”,汉代人叫做“五常”。儒家的德目非常广泛,如“孝”“诚”“直”“勇”“刚”“宽”“恭”“敬”“廉”“让”“惠”等,都是儒家所信奉的伦理道德价值。 儒家的古典学自西汉被确立为正统的学问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末。而佛道整体上是非正统性的,但在不同时期,两者或多或少也有正统性。如汉初道家或黄老学具有官方性,《老子》这部经典在汉初七十年变成了官方的经典。在唐代,老子和道家受到特别的礼遇;佛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南朝的梁武帝热衷于佛家,唐代也有皇帝热衷于佛家,佛家在唐代最兴盛。中国古典学整体上奉行三教并行又有主次之别。在三教争论中,儒家自居于正统,将道家和释家看成是异端,宋明新儒家往往以释道为空无,声称的虚无性,重建意义和价值信仰,并寻找根源论的基础。古典学的方法和形态的不同,所引发的正统、道统与非正统和异端的争论,是意义和信仰之争;为了调和、弥合各经典的差异性,使之井然有序和具有统一性,佛学不同宗派对各类经典的地位和意义的判别、判定的教相判释论,其实也是各宗派确立本宗的正统性和权威性的一种方式。 整体上说,古典学中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原动力和最普遍的价值。正如金岳霖所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金岳霖:《论道·绪论》) 作者: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