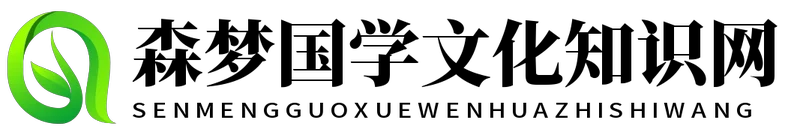摘要:在先秦儒学中,“四端”代表道德情感,“七情”代表自然情感,孟子强调“四端”的超越性。至宋代理学,朱子以“性(理)/情(气)”的二元模式将“四端”置于形下之域,弱化了孟子关于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划界。前期的“四七之辩”在朱子学的框架之内展开,退溪力图以“理发”凸显“四端”的超越性,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异层的两种情感。而栗谷恪守朱子“情即气”的界定,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同层包含的关系,并以至善之“意”作为引导“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
关键词: 四端 七情 道德情感 李退溪 李栗谷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东亚近世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从东亚的视野看儒学,更能完整呈现出儒学义理内在展开的多种可能性。性理学是中国朱子学的延续和发展,在继承朱子哲学整体框架的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化和地域化特色。前期儒学的“四端七情”论辩,在实质上是朱子学内部关于“情”的归属和来源问题的争论,其所指向的哲学问题是如何对道德情感予以定位。
这场辩论有两次,一次是在李滉(退溪)和奇大升(高峰)之间,另一次是在李珥(栗谷)和成浑(牛溪)之间。这场论辩的争论焦点集中于“四端”和“七情”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退溪与高峰、栗谷的分歧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四七同异,退溪主张“四端”与“七情”来源不同,因而异质异层,高峰、栗谷主张两者都是气发,属于同质同层,七情包含四端;第二,关于四七善恶,退溪主张“四端”至善无恶,“七情”有善有恶,而高峰、栗谷主张四七都有善有恶,四端也有不中节的情况[1]。
双方观点的核心在于“四端”的定位问题,也就是道德情感的定位问题。笔者曾经撰文对从东亚儒家情感哲学内在演进的视角梳理“四端”“七情”的观念史[2],在该文“述史”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析论”,力图聚焦“四七论辩”所关涉的哲学问题并展开理论分析。
一、中国儒学关于道德情感的论说
“四端”之说源自孟子,“七情”之说源自《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讲,“四端”归属于“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3],而“七情”则归属于“自然情感”(natural emotion)。儒学史上对道德情感的关注源远流长,关于其定位问题亦争讼不已。
在《论语》中,孔子随机指点了一系列具有鲜明道德属性的情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在孔子看来,以上文本中提到的“爱”“不安”“耻”“恭”“敬”“忠”“好”“恶”等情感并非人人生而普遍具有,他鲜明地将这些情感与“仁”关联起来,强调只有“仁者”才能真正表现出这些情感,换言之,只有在相应的伦理情境中恰当地表现出这些情感才能配称为“仁者”。这些情感中最为典型的是“不安”,对于这种情感,新儒家学者牟宗三进行了细致的阐发:“宰予说‘安’,即宰予之不仁,其生命已无悱恻之感,已为其关于短丧之特定理由所牵引而陷于僵滞胶固之中,亦即麻木不觉之中,而丧失其仁心,亦即丧失其柔嫩活泼、触之即动、动之即觉之本心。是以不安者即是真实生命之跃动,所谓‘活泼泼地’是也。此处正见‘仁’。”[4]如果我们把人之喜怒哀乐的心理状态称之为“自然情感”的话,那么这种不安悱恻之情可以称作“道德情感”。在孔子这里,这种“不安”“爱人之爱”的情感是德性的基础。
孔子并没有对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的关系做出具体论述,但是《论语》中曾两次出现同一句话,耐人寻味: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
其中出现了两个“好”字,在孔子那里似乎并非有所区分。但是进一步分析,所谓“好色之好”属于一种自然情感,而“好德之好”则属于一种道德情感,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理想层面对“德”的喜好应当如同对“色”的喜好一样是自然而然且人人皆然,但是现实中之“好德”却只有少数君子经过克己复礼的修养工夫才能做到。在孔子看来,“好德”本身应当是超道德的,应当是从容中道而非勉力所至,应当是“从心所欲”而自然不逾乎规矩的。
在儒学史上,第一个将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相区别的人是孟子。他继承了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体察,并进行了系统化的整合,提出了“四端说”作为性善论的核心观念。关于“四端说”,《孟子》一书中有两处表述,稍有差异: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又称为“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情感状态分别作为“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的基础,因而这四种“心”无疑是道德情感,有强烈的价值属性。在《公孙丑上》中,孟子将这四种道德情感称之为“四端”,对于这里的“端”,赵岐注云:“端者,首也。”(《孟子正义》)朱熹注云:“端,绪也。”(《孟子集注》)也就是端倪、兆头、萌芽之意。
孟子的意思是强调“四端”尚不能等同于“四德”,“端”是“德”的潜在形态,“德”是“端”的完成形态,从“端”到“德”需要下文所讲的“扩而充之”的过程,道德善恶的分化也正在于是否践行这个“扩充善端”的工夫。而在《告子上》中,孟子没有使用“四端”的说法,而直接表述为四种道德情感就是德性。这说明,在孟子那里,“四端”(“四心”)与“四德”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都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四端”经过扩充必然推至“四德”。
与孔子所谓“好德如好色”的类比逻辑相一致,孟子也将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进行类比: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孟子以众人对于味觉、听觉、视觉等方面的普遍性来论证“心”对于道德原则追求的普遍性,进一步,他通过“口悦刍豢”的自发性来说明“心悦理义”的必然性。“理义”是道德原则,而“悦理义”则是一种道德情感,孟子力图说明,道德原则植根于道德情感,而这种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一样是天赋而普遍的。如同人对于美味的喜爱是天性本然,人对于道德原则的喜爱之情也应当是人之本性中自然而然的倾向,道德情感(如“四端”)的发用流行并不带有任何强迫性,而是人依据本性而自觉自愿的活动。
尽管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都具有普遍性,但是孟子特别强调两者的差别,典型的就是他关于“大体”与“小体”之间的区分: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所谓的“大体”是指“心之官”,即能思的主体,也就是道德理性;所谓“小体”是指“耳目之官”,即感觉、情绪、等。孟子指出,耳目之官不能够“思”,因此也不过是一种被动性的“物”,在与外物相交涉之时受外物而沉溺、做作;只有心能够“思”,这是一种道德理性的自我反思,用道德原则来衡断、裁定行为的正当性,经过这种反思作用就能够成就道德行为。孟子强调这种“心官之思”于人而言是先天禀赋的,并不是后天习得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孟子所讲的“思”尽管是一种道德理性的反思活动,但这并不是与道德情感相分离的纯粹知性的反思,而是由道德情感扩充而成的道德理性。[5]孟子关于“大体”“小体”的区分明确突出了道德理性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且指出应当的处理方式是“先立其大”,也就是确立“心”的主宰地位,而“耳目之官”听从于“心”的命令。尽管孟子这里讲的“心之官则思”的理性反思性与他讲“恻隐之心”发动时的情感直觉性存在着差别,但这种模式区分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的思维模式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尽管孟子并没有完整论述“七情”的内容,但在他心中“四端”与“七情”之间的差别是泾渭分明的。
在孔孟那里,最重要的道德情感无疑是“仁”。据统计,《论语》一书中“仁”共出现了109次,其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爱人”,体现出对人的生命价值予以肯定和培护的深厚情感。[6]其后孟子从内外两个方面拓展了孔子“仁”的学说:一方面向内将“仁”追溯为先天固有的“恻隐之心”,另一方面向外由“亲亲”推广至于“仁民”和“爱物”。孟子身后,“仁”这种道德情感沿着“个体性”“普遍性”和“超越性”三个向度演进:或者成为个体内在的道德根基,或者成为社会普遍伦常规范,或者成为宇宙超越的本体。
第一,在个体性向度上,《中庸》将“仁”定位为“成己”的德性,引向内在的心性本体;荀子强调“仁者自爱”(《荀子·子道》),将道德情感的重心指向个体自我的修身实践,其后宋明儒者所讲的“觉”“识痛痒”“不麻木”等心理状态都是“仁”的道德情感的体现。
第二,在普遍性向度上,汉儒贾谊将“兼爱”“博爱”等原属于墨家的思想纳入儒家“仁”的内涵(参见《新书·道术》),使得仁爱包容了以往各家所提出的普世之爱;唐儒韩愈直接说“博爱之谓仁”(《原道》),以此作为儒家区别于佛道思想的根本特质;宋儒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二程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二程遗书》卷二上),将“仁”的对象和范围拓展到最广大的时空场域。
第三,在超越性向度上,《易传》将“仁”与“元”相对应,使之与“天地之生生”相关联,从而赋予“仁”以形上学内涵;董仲舒将“仁”视为“天”或“天心”(《春秋繁露·俞序》),同时也作为“气”的一种形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使之参与儒家宇宙论之建构,具有了实体性和超越性的意义;朱子将“仁”提升为“天地生物之心”(《仁说》),成为宇宙运行的目的、万物之所以生生的内在根据(“生理”)。[7]
朱子完成了对于“仁”这一道德情感的形上化进程,在“理/气”二元的本体论架构中,“仁”属于“理”。在这个结构中,“仁”脱离了原本“爱人”的情感属性而成为高度理性化的伦理规范和本体观念。而在孟子那里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由于保持着情感属性而被归入“气”的范畴。这样一来,在孟子那里“爱为仁端”的一层结构在朱子这里变成“仁情”的两层结构。
这种二元模式推广到朱子对孟子“四端”的诠释中,他引入了“心统性情”的理解模式,以“理/气”“性/情”“未发/已发”“形上/形下”等一系列二元框架来分别心性过程。在朱子“中和新说”中,“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这里所有的情感现象(无论“四端”还是“七情”)由于都是已发,因而都归于“情”的范畴[8],也就是归入“气”的范畴。原来在孟子那里的“四德”与“四端”是完成状态和萌芽状态的关系,而在朱子的理解中,两者是异质异层的关系,分别属于“理”与“气”“性”与“情”两个层面:
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9]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10]
由于朱子认为“性即理”,就将心性论上的“性情”关系与本体论上的“理气”关系相关联,自然得出“情即气”的结论。因而,在朱子学中,“四端”“七情”都应当归属于气。这里,孟子所强调的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界限被弱化了。
二、退溪关于道德情感地位的凸显:“四七异质”
关于“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本人的表述是有前后矛盾的:一方面他讲“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11],似乎将“四端”和“七情”区分得泾渭分明;另一方面他又讲“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12],似乎说“四端”与“七情”相互交叉,难以区分。这就增加了后学对这一问题的疑惑和歧见,也为不同的阐释留下了巨大空间。
朱子身后,黄榦、胡炳文、程复心以至于的权近、柳崇祖、郑之云等人都沿着区分“四端”与“七情”的方向上前进,这个思路在李滉(退溪)这里得到了完成。
在论辩中,退溪的立场一以贯之,强调“四端”与“七情”的差异性:
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13]
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14]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的是,退溪以朱子学的继承者自任,因此坚持“理气不离不杂”的本体论信念。换言之,不论退溪怎样论证“四端”“七情”的区分,他都不否认“四端”“七情”都是理气和合的存在,“主理”“主气”的差异只存在于“情”的源头上,而不存在于“情”的属性上。所以退溪只在“发”上分理气,他在最初讲“四端之发,纯理”,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四端是纯理”。
在经过奇大升(高峰)的质疑之后,他改用了更为精审的“理发气随”“气发理乘”的“互发说”,并进一步强调区分主理、主气并非割裂理气关系。这就表明,退溪并未否认朱子关于“情是气”的定位,只是力图强调“四端”是一种特殊的情,由于“四端”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这种情必然与一般的自然情感有所区别,与超越的宇宙本体相关联。与孟子到陆王一系的心学传统相区别,退溪将这种宇宙本体归之于“理”而不是“心”,因此只能以“理发”来表明“四端”的超越性、至善性。
正如韩国学者崔英辰所指出的:“确立四端的纯粹善性的理论根据是当时退溪的重要课题。理发说不是为了说明理的属性,而是为了树立四端的形而上学的根据而提出的命题,是为了从质的角度区分四端与七情而把它们分属于理气,并将其所从来分别配属于理气。换言之,是为了将四端纯善性的论据放在纯善之理(即性)上才把四端解释为理发。”[15]
实际上,在“四七论辩”中,退溪关于“四端”的论述包含了孟子学与朱子学的矛盾,他纠结于“四端发于理”和“四端是情(气)”之间,这个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直到68岁时(1569)向宣祖所上的《圣学十图》中,在第六《心统性情图》(见“图1”)中用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图示来表明以上两种说法同时成立。
与其他九图有所不同,《心统性情图》是由三个图组合而成,《上图》是元儒程复心所作,而《中图》和《下图》是退溪自作。比较这两个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图》的“性圈”之中只有“仁义礼智”,而《下图》的“性圈”之中除了“仁礼信义智”之外还有“清浊粹驳”,说明中图所论的“性”是本然之性未受气质影响的理想状态,而下图所论的“性”是本然之性堕入气质之中的现实状态,前者是至善无恶的,而后者是有善有恶的。
退溪对于《中图》所配的图说如下:
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16]
夫如是,故程夫子之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只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17]

图1 李滉《圣学十图》第六图《心统性情图》
退溪指出,《中图》的性是本然之性,所发之情是“四端之情”,因此都是至善无恶的,这里实际上就是在表达“四端是理之发”的意思。不仅是“四端”,就连“七情”也是至善的(无不中节),因此图中明确标示:“就善恶几,言善一边。”这里的“四端”与“七情”尽管仍然有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差别,但在地位上属于同一层次。这实际上讲的是圣人境界,情之发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退溪在后面针对论敌可能引用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来质疑此图的情况(事实上后面的栗谷在答复牛溪第七书时就是这么做的),解释道:尽管在现实中总是理气不离的,“性”必然堕入气质之中,但是如果不在理想状态下讨论本然之性发为四端之情的情况,就不能凸显出性善的本义。退溪这里实际上站在孟子的立场上为性善论和四端说进行辩护,申明孟子所要阐明的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性情关系,因此不能用气质来“污染”四端。
退溪对于《下图》所配的图说基本上就是他在“四七之辩”中的核心观点了:
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之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之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18]
退溪在这里是内在于朱子学的立场立论的,由于图中所标示的“性本一因在,气中有二名”,所以现实中的“性”兼具理气、有善有恶,这样就“理发气随”和“气发理乘”两种情况,就有“四端”与“七情”的分别。但退溪在此图中并没有像郑之云的《天命图》那样把“四端”与“七情”分列左右两边,而是上下排列,目的是表示一个逻辑上的先后过程,因为本来的情是至善无恶的,而受到“气”的影响后才产生恶的结果。退溪的这种排列应当是吸收了高峰对于《天命图》“离析太甚”的批评意见后的有意调整。
由此可见,退溪处理孟子学与朱子学关于“情”的问题采取了“并行不悖”的策略,在宏观上沿用朱子“心统性情”“性发为情”的大框架,但是微观上将“性”的内容区分为理想状态的“本然之性”和现实状态的“气质之性”,由之所发的“四端”“七情”也就有理想状态(圣人之境)和现实状态(常人之境)的区分。更为严格地讲,根据退溪的立场,“四端”无论在理想状态还是在现实状态都是至善的,也就是“理发”,这是凡圣所同;关键的区别在于“七情”,圣人之七情是至善的,而常人之七情有善有恶,这是凡圣所异。
在退溪所画的《中图》中,尽管没有注明“理发”的字样,但是根据义理,由本然之性所发必然是“理发”,而“四端”与“七情”并列置于“性”之下,似乎说明圣人的“四端”“七情”都是“理发”。而在《下图》,退溪明确注明常人之“七情”是“气发而理乘之”。退溪的意思似乎是:就自然情感而言,圣人之七情源自本然之性(纯理),其“无不善”是先天必然的;而常人之七情源自气质之性(兼气),其为善是发而中节,是后天工夫所致。
细究之下,这种理解并不符合朱子的观点,朱子认为圣人同样也有气质之性,这一点与常人不异,只不过圣人的气质“清明纯粹”,而常人“昏暗驳杂”。所以圣人的“七情”也应当源于气质之性,其发而皆中节是气质条件优越的结果,而不是“理发”。因此,在笔者看来,退溪若为避免两图中“七情”所可能引起的这种矛盾的话,应当删去《中图》中的“七情”部分;而《中图》与《下图》的关系并非并立,《中图》包含于《下图》之中,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部分。
总之,无论《中图》还是《下图》,退溪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四七之辩”的立场,捍卫“四端”作为道德情感的超越性和至善性。
三、栗谷关于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以意导情”
栗谷对于“情”笼统观之,不重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区分,基本上沿袭朱子关于“情”属于气的观点,强调“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一途”。将“四端”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情,把道德情感自然化,这是栗谷心性论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他与退溪的关键性区别。
栗谷在给门人安应休(字天瑞)的信中写道:
天命之性,理之在人者也,人非气耶?率性之道,理之在事物者也,事物非气耶?达道之道,理之在情者也,情非气耶?是故情非和也,情之德乃和也。情之德,乃理之在情者也。若以情为和,则将放情纵欲,无所不至矣,其可乎?人之喜怒哀乐,犹天之春夏秋冬也。春夏秋冬,乃气之流行也。所以行是气者,乃理也。喜怒哀乐,亦气之发动也。所以乘是气机者,乃理也。[19]
栗谷将人和事物都视为“气”,同样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就如同天之春夏秋冬一样都属于“气”,栗谷的逻辑很明确:所有的“情”都是已发,已发就是显示在经验世界,因而必然是气之流行发用。这种理解完全是依照朱子的“中和新说”立论。同时,栗谷还强调在“气”的动静背后还有“理”乘之而动静,所以“情”背后是“理”在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这种“理之在情者”不同于“情”,而被称为“情之德”,如同朱子所说的“仁者,心之德、爱之理”[20]。《中庸》把喜怒哀乐的情感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之为“和”,栗谷强调,这种“和”的状态已经不是“情”本身了,而是“情之德”或者说是“情之理”了。栗谷认为如果把“和”错误地理解为“情”本身的话,就会导致放情纵欲的严重后果,这表达出他对于自然情感的不信任,强调必须“以理宰情”。
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既然“理无造作”,高高在上,又如何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主宰“情”的运行呢?在这个问题上,栗谷非常强调“意”的作用。他在朱子“心统性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心兼情意”或“心通情意”的命题:
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21]
人心道心,通情意而言者也。[22]
栗谷这种说法同样是根据朱子所论而发挥之。朱子认为:
意者,心之所发也。[23]
李梦先问情、意之别。曰:“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后用。”[24]
问:“情、意,如何体认?”曰:“性、情则一。性是不动,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25]
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26]
综合以上文本,朱子所讲的“意”大约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意”是心之所发,用以表示意向的心理活动;第二,“意”是由未发到已发的关节点上表现出来的动机;第三,“意”的作用对象是“情”,引导“情”发用的方向。
明儒罗钦顺继承了朱子的思路,对“意”进一步加以阐述:
先儒言:“情是性之动,意是心之发。”发动二字亦不相远,却说得情意二字分明。盖情是不待主张而自然发动者,意是主张如此发动者。不待主张者,须是与他做主张,方能中节。由此心主张而发者,便有公私义利两途,须要详审。二者皆是慎独工夫。[27]
所谓无意者,无私意尔。自日用应酬之常,以至弥纶、参赞之大,凡其设施、运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无?惟一切循其理之当然而已。无预焉,斯则所谓无意也已。[28]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则思,是皆出于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为也。圣人所谓“无意”,无私意耳。……故《大学》之教,不曰“无意”,惟曰“诚意”;《中庸》之训,不曰“无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门,积德之基,穷理尽性必由于此,断断乎其不可易者,安得举异端之邪说以乱之哉![29]
罗钦顺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同意朱子“意是心之发”的界定,并进一步申论“有心必有意”,强调“意”的必然性;第二,强调“意”对于“情”的引导功能,“情”必须有“意”来作主张才能中节;第三,“意”除了行为动机、意向的含义之外,还包含“设施、运用、斟酌、裁制”等理性功能,“意”与“思”相互关联;第四,经典中“无意”“勿意”中的“意”是“私意之意”,不是“诚意之意”,“诚意”工夫是工夫着手处。
栗谷继承了朱子、罗钦顺讲“意”的基本含义,并进一步予以充实完善。他在回复牛溪论四七的第一书中提出,“意”有计较、商量、精察的内容:
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30]
栗谷指出,在“情”之发动时,“意”起作用,精察情发用的方向而引导其合乎正理,这样就达到善的结果,反映在“心”上就是“人心听命于道心”;反之,如果“意”不起作用或作用无效,那么情就完全顺从,人心主宰、道心沉沦,造成恶的结果。这里的“意”包含着道德理性的内容,所谓“精察”“计较”是一个认知、判断、思考的理性过程。栗谷这里实际上是强调道德理性对于自然情感的指导作用,这较之于朱子以“意”单纯作为行为意向和动机的说法增加了明确的理性内涵,而与罗钦顺的思路一脉相承。栗谷关于“自修莫先于诚意”的工夫进路与罗钦顺“以诚意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的说法也非常接近。
其后,栗谷沿着“意缘情计较”的思路,进一步强化了“意”的理性功能:
“情意二歧、理气互发”之说,不可以不辨。夫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更无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动为情。”情是感物初发底,意是缘情计较底,非情则意无所缘。故朱子曰:“意缘有情而后用。”故心之寂然不动者,谓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谓之情;心之因所感而䌷绎思量者,谓之意。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31]
惟其气质不齐,其动也,气或不清,不能循理,则其发也不中。而驯至于恶,自其初动而已然,非厥初必善而厥流乃恶也。故周子曰:“诚无为,几善恶。”“诚无为”者,未发也。“几者”,动之微者也。动之微也,已有善恶几,乃情也。意者,缘情计较者也,情则不得自由,蓦地发动,意则缘是情而商量运用。故朱子曰:“意缘有是情而后用。”[32]
栗谷把这种“意”的作用称之为“䌷绎思量”“商量运用”,依然强调其理性作用。他继承了朱子“未动而欲动者意也”的说法,强调“意”是在情之发动的初始,即未发已发的交汇点(“几”)上起作用,有了“意”的这种理性判断的活动,“情”就避免了无原则的泛滥,在发动的第一时间就受到引导和制约。
有鉴于“意”的重要作用,栗谷主张以“诚意”作为工夫论的核心:
学者当以“诚其意”为用功之始,而“戒慎恐惧”于不闻不睹之地。[33]
如欲诚意,则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得之,恶恶如恶恶臭而决去之,幽独隐微之中敬畏无怠,不睹不闻之时戒惧不忘,必使念虑之发莫不一出于至诚,以尽其诚意之实。[34]
相对于退溪以“敬”为核心的工夫论,栗谷以“诚”作为工夫的核心。栗谷“诚意”说的思想源头无疑是《大学》的“诚意”与《中庸》的“慎独”,体现出道德理性的高度自律性,是一种“自慊而不自欺”的境界。按照《大学》的例子,“诚意”就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过程,其中既包含着对于“好色”和“恶臭”的认知和判断过程,也包含着对于“对好色之好”与“对恶臭之恶”的情感反应和实践行为。这里让我们不禁联想到王阳明所理解的“诚意”:
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35]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36]
阳明所讲的“诚意”就是于一念发动处而有所好恶,这种能够给予正确好恶的主体就是“是非之心”,也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尽管栗谷作为一个虔诚的朱子学者,对于阳明学视之为异端,但他的“诚意”思想与阳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仔细品味栗谷所说的“以意导情”,得出一个印象:栗谷所说的“意”充当了孟子(阳明)所说的“是非之心”的地位和功能,换言之,尽管栗谷并不将作为道德情感“四端”视为超越性的本体,但是又在“七情”之上提出了“意”作为是非判断的依据来引导“情”的发用。栗谷实际上是在朱子所规定的“心—性—情”三元心性论结构之外,加上了第四元“意”,通过“意”来弥补“情”由于“四端气化”而带来的道德约束力不足的问题。
栗谷在范畴体系和表述方式上与胡炳文、权近的思路相似,在“性发为情”之外重提“心发为意”,但是将含义反过来理解,“意”成为至善的,而“情”成为可善可恶的,在某种意义回归于朱子的定义。可以说,栗谷是在朱子学内部,以朱子的范畴(“意”)弥补了朱子的问题(“四端是气”)。总之,在功能的相似性上,我们可以把栗谷的“以意导情”思路视为“四端”的替代性方案。
综上所述,对于先秦儒家所提出的道德情感的定位问题,朱子以“性(理)/情(气)”的二元模式将其置于形下之域。在朱子学的框架之内,退溪力图以“理发”凸显“四端”的超越性,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异层的两种情感;而栗谷恪守朱子“情即气”的界定,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同层包含的关系,并以至善之“意”作为引导“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相较而言,对于道德行为的主要动力问题,退溪强调道德情感的培养,栗谷则强调道德理性的发挥。
注释
[1]参见谢晓东:《朱熹与“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兼论恻隐之心、情境与两种伦理学的分野》,《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2]参见卢兴:《“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3]本文所讲的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力图与西方伦理学所讲的“moral sense”或“moral sentiment”有所区别。牟宗三曾用“本体论的觉情”(ontological feeling)一词来定位儒家的道德情感,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7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08页。
[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6卷,第234-235页。
[5]蒙培元指出:“从根本上说,孟子的道德理性学说不是建立在‘知性’或‘智性’之上,而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和直觉之上。特别是道德情感,既然是理性的基础,就更不能没有自我体验,而体验只能是情感体验。所谓‘思’的认识,只能在‘悦’的体验中发生。”参见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6]参见卢兴、吴倩:《儒家“仁德”的内在理路和逻辑层次》,《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2期。
[7]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8]陈来指出:“情在朱熹哲学中的意义至少有三种,一是指作为性理直接发见的四端,二是泛指七情,三是更包括某些具体思维在其内。”(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
[9](宋)朱熹:《玉山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588-3589页。
[1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第15册,第236页。
[1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三,《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第16册,第1908页。
[1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第18册,第3178页。
[13][韩]李滉:《与奇明彦(己未)》,《定本退溪全书》第3册,首尔:退溪学研究院,2006年,第36页。
[14][韩]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定本退溪全书》第3册,第113页。
[15][韩]崔英辰:《韩国儒学思想研究》,邢丽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16][韩]李滉:《圣学十图·心统性情图说》,《定本退溪全书》第11册,第137-138页。
[17][韩]李滉:《圣学十图·心统性情图说》,《定本退溪全书》第11册,第138页。
[18][韩]李滉:《圣学十图·心统性情图说》,《定本退溪全书》第11册,第138页。
[19][韩]李珥:《答安应休》,《栗谷全书》卷十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7-448页。
[20](宋)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朱子全书(附外编)》第6册,第244页。
[21][韩]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卷九,第346页。
[22][韩]李珥:《答安应休》,《栗谷全书》卷十二,第450页。
[23](宋)朱熹:《大学章句》,《朱子全书(附外编)》第6册,第15页。
[2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附外编)》第15册,第243-244页。
[2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附外编)》第15册,第244页。
[2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附外编)》第15册,第244页。
[27](明)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5页。
[28](明)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上,第99-100页。
[29](明)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下,第106-107页。
[30][韩]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卷九,第347页。
[31][韩]李珥:《圣学辑要·修己第二·穷理章第四》,《栗谷全书》卷二十,第845页。
[32][韩]李珥:《答安应休》,《栗谷全书》卷十二,第449-450页。
[33][韩]李珥:《四子言诚疑》,《栗谷全书拾遗》卷六,第2072页。
[34][韩]李珥:《东湖问答》,《栗谷全书》卷十五,第584页。
[35](明)王守仁:《大学问》,《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二十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1018页。
[36](明)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三,第121页。
作者:卢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来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