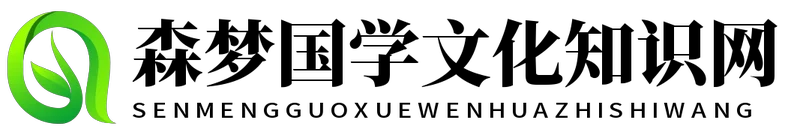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诠释观点都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因而其意义是确定的,诠释就是对作者意图的重建。如何重建作者的写作意图呢?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提出了语法阐释与心理阐释相结合的诠释方法。中国古代的训诂学,相当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语法阐释。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相当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心理阐释。然而,借助于这两种诠释方法,就能准确地、无可争议地阐释出作者的原意了吗?从诠释史来看,特别是对被奉为经典的文本的诠释史来看,历来大多是异说纷呈,意见难以一致。几乎每一个诠释者都宣称自己读懂了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然而往往又会遭到其他诠释者的批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试以《道德经》首章首句的诠释为例,来对此现象作一探讨。 老子《道德经》乃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幢丰碑,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智慧明珠。古今中外,注释《道德经》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道德经》言简意丰,其哲理诗般的语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故而历来异解纷纭,莫衷一是。仅《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这几个字,各种释义,即大相径庭。要统计古今注家对“道可道非常道”有多少种解释,几乎不可能。今就笔者所见的几种解释,列举如下。 1、 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这种观点将“可道”的“道”字理解为言说,将“常道”理解为永恒常在之道,认为永恒常在之道不可以言说。 持此种观点的人为《道德经》注家的主流。不过,此一主流又须细分为两个支流:一部分人直接断言“道不可言说”,从而逻辑地否认了有可以言说之道的存在;另一部分人则只是强调“常道不可言说”,并不否认存在着可以言说之道。现分别述之。 (1)道不可言说。 战国末期的韩非在《解老》篇中即以“理”与“道”的区别来说明“道不可道”。他说:“理者,成物之文也”,“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可见,“理”是具体事物的规定性,韩非称之为“定理”。定理是可以言说的。但定理随物之存亡而存亡,故不能常。“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统辖万物之理,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故常存不灭。“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韩非子》卷六) 唐代道士成玄英说:“道以虚通为义,常以湛寂得名。所谓无极大道,是众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谓可称之法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辩,不可以心虑知,妙绝希夷,理穷恍惚。……可道可说者,非常道也。”(《道德经义疏》)其意为:道本湛寂,其用虚通,不可测知,当然更不可言说。一说就受到了语词的限制,就不是虚通之道,而是可称之法了。 北宋王安石说:“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则是其迹也。有其迹,则非吾之常道也。”(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其意为:凡可言说者,皆是道之“迹”,而非道之本。道之本,即道本身,亦即“常道”,是不可言说的。 北宋道士陈景元说:“夫道者,杳然难言,非心口所能辩,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议,在人灵府自悟尔,谓之无为自然。今标道者,已是强名,便属可道。既云可道,有变有迁,有言有说,是曰教典,何异糟粕。”(《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其意为:道只可体悟,不可言说。若可以言说,就有变迁,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宋徽宗说:“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当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时焉,当可而应,代废代兴,非真常也。”(《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无始曰”与“又曰”云云,皆引《庄子•知北游》语。徽宗意为:道若可言说,就跟事物、四时一般,处于变迁之中,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其观点与陈景元大致相同。 北宋末江澂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与物相去远矣,故不可以言论。”(《道德真经疏义》)道精物粗之论出自《庄子》。《庄子•天下》篇评论关尹、老聃的学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江澂之意为:道精物粗,粗者可说,精者不可说。 南宋林希逸说:“道本不容言,才涉有言,皆是第二义。常者,不变不易之谓也。可道可名,则有变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则无变无易。”(《道德真经口义》)这种说法明显受到了佛教所谓“第一义不可说”的思想的影响。 南宋道士褚伯秀曰:“道本至无,不容称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明代释德清说:“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犹言也。意谓真常之道本无相无名,不可言说。凡可言者,则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太上老子道德经解》) 近代魏源说:“至人无名,怀真韬晦,而未尝语人。非秘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语显而名迹求者也。及迫关尹之请,不得已著书,故郑重于发言之首,曰道至难言也,使可拟议而指名,则有一定之义,而非无往不在之真常矣。”(《老子本义》) 近代梁启超说:“道本来是不可说的,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本来常住之道了。”(《老子哲学》) 当代冯友兰说:“道是‘无名’,没有任何规定性。言语所说的都是事物的规定性,对于没有规定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说了。”“可以言说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2册) 任继愈认为:“《老子》书中的‘道’是不能用文字或语言表达的、神秘的精神本体。”他的翻译是:“‘道’,说得出来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老子新译》) 钱钟书说:“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又说:“责备语文,实繁有徒。要莫过于神秘宗者。彼法中人充类至尽,矫枉过正,以为至理妙道非言可喻,副墨洛诵乃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耳。……《老子》开宗明义,勿外斯意。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也。”(《管锥编》第二册) 张松如说:“道、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其解说曰:“单个的东西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任何词(语言)都已经是在概括。所以老子认为,‘道’(自在的)是不可言道,无以名之的;可以言道,可以名之的‘道’(观念的),便不是恒道,不是永恒绝对之‘道’。”(《老子说解》) 陈鼓应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其解说为:“这个‘道’是形而上的实存之‘道’,这个形上之‘道’是不可言说的;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用来表述它,任何概念都无法用来指谓它。”为什么道不可说呢?“由于‘道’的不可限定性,所以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指称它。”(《老子注译及评介》) 李泽厚说:“‘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便不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 (2)常道不可言说。 西汉严遵说:“可道之道,道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昼不操烛,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烛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北宋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引)严遵在这段话里明显把道分为“可道之道”与“常道之道”,认为“可道之道”可彰显而传于人,“常道之道”则自然而然,不可授受。 汉代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认为,可道之道,即经术政教之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常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辉,灭迹匿端,不可称道。”这里也将道分为“可道之道”和“常道”。常道无为无事,不见其有所作为,故不可言说。 曹魏王弼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老子注》)一些人认为王弼开了“道可不道”的先河。(参见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但王弼在这段话里明确提出有“可道之道”。从逻辑上说,“可道之道”当然也是一种“道”。可见,王弼只是认为可道之道非常道(“非其常”),常道不可道。 北宋吕惠卿曰:“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时乎殆,则非常道也。……则常道者,固不可道也。”。(《道德真经传》)其意很明显:可道之道也是道,但不是常道。常道不可言说。 北宋苏辙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后可常耳。今夫仁义礼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为义,而礼不可以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后在仁为仁,在义为义,在礼为礼,在智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变,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德真经注》)从“莫非道也”可以读出苏辙主张“可道”与“常道”皆是道。 两宋之际的程俱说:“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于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则圣人未敢以示人。非藏于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以示人焉耳。”(《北山集》卷十三《老子论》)其意为:圣人以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为世人确立言行的准则,至于常道、常名则不可得而道、得而名以示人。 元代丁易东说:“首一道字与下常道字,皆是言道之体,特可道之道字,则指世人所谓道而言之,若曰吾所谓道者,非世人可以指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则非吾所谓自然之常道矣。……世俗之所谓道者,……盖儒者之所谓道,乃日用通行之道,而老子之所谓道,乃专指虚无自然者为道。”(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 明代李贽说:“不知而自由之者,常道也。常道则人不道之矣。舍其所不必道,而必道其所可道,是可道也,非常道也。”(《道德经解》)其意为:常道乃自然之道,人日行其道而不自知。常道无人说,也不必说。因此,人所说者,不是常道,而是可道之道。 明代道士王一清说:“有世间之道,有出世间之道。世间之道,有形有名,有理有事,故可道可名也。出世间之道,无形无名,视不见,听不闻,故不容言,不能名也。常者,常住不灭之意。……故知可道可名者,乃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君臣父子政教之道之名,而非真常之道之名也。”(《道德经释辞》)其意为:世间之道乃可道之道,出世间之道才是真常之道。 近代丁福保说:“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此道字,非儒家之所谓道,即本经五十九章长生久视之道,乃道家之专门名词,谓真常不灭之道也。”(《老子道德经笺注》) 近代王力说:“既云道可道非常道,则常道乃不可道者也。道之本体,是谓常道。言及本体,无法以形容之,故曰不可名,又曰强为之名也。然则道之本体,已离言说;欲得其真,须凭直觉。盖老子五千言,皆可道之道耳。”(《老子研究》) 近代高亨说:“道可道,犹云道可说也。……道可道非常道者,例如儒墨之道,皆可说者,非常道也。……其意以为吾所谓道之一物,乃常道,本不可说也。”(《老子正诂》)他后来又在《老子注译》中详细阐释说:“老子说:道之可以讲说的,就不是永远存在的道,如儒家所谓‘道’便是,而我所谓的‘道’(宇宙本体),是不可以讲说的,是永远存在的‘常道’。” 当代卢育三说:“这句是说,道,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常道。在这里,老子把道区分为两种:一为不可道之道,一为可道之道。不可道之道,即所谓常道,是永恒的、不变的道;可道之道是暂存的、可变的道。”(《老子释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2、道可以言说,但不是常俗之道(或常人所谓的道、寻常的道、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持此种观点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主张“道可以言说”,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然而他们在“常道”的解释上,又不尽相同。或解释为“常俗之道”,或解释为“常人所谓的道”,或解释为“寻常的道”,或解释为“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唐代道士李荣曰:“道者,虚极之理也。……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道德真经注》)其意为:道即虚极之理,理是可以说的,所以道可道。但这个道不是人间常俗之道。 北宋司马光说:“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常人之所谓道者,凝滞于物。”(《道德真经论》) 北宋陈象古曰:“可道谓众人之所知者也,可名谓众人之所见者也。虽可知可见,未能尽道之妙理也。故众人常道者,非所谓道也;众人常名者,非所谓名也。”(《道德真经解》) 南宋廖粹然曰:“道:元始。可道:字之曰道。非常道:不是寻常所言道者。”(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元僧德异(号休休庵)说:“道本无言,因言显道,可以说也,非寻常之道,妙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元代喻清中说:“其所谓道,未尝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非常人之所能道。”(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引) 元代吴环中说:“老子之所谓道,非世上寻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见其首,随之而不见其后。此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寻常之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引) 当代周生春说:“前一个‘道’指宇宙的本原和实质,后一个‘道’指解说。常:普通的,平常的。这句话以往多解释成:‘道’,如果可以说得出来,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这种解释偏离了《老子》的本义。(帛书)甲本、乙本‘道可道’后均有一‘也’字。据此,可知这句话应解释成:‘道’是可以表达的,它不是普通的‘道’。《老子》通篇说的就是‘道’。……显然,如果‘道’不可言传,那么《老子》五千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子注译》,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当代郭世铭则认为,“第一个‘道’字是《老子》的专用术语,是名词。后两个‘道’字都是动词‘说’的意思”。他认为“常”字“既可以解释为‘永恒’、‘永远’,也可以解释成‘经常’、‘一贯’、‘一直’、‘坚持’。两种释义的区别在于:前后包括将来,后来不包括将来,只说到迄今为止。”他主张在此处作后一种解释。他说:“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他还指出:“如今‘道不可道’、‘道不可名’差不多已成为研究《老子》的主导思想,人们对此也早就习以为常,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大家都说《老子》是讲‘道’的,而大家又都说老子认为‘永恒的道’是说不出来的。那么,《老子》一书究竟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不永恒的道’,还是在讲‘说不出来的道’?如果是前者,又何必去讲它?如果是后者,《老子》怎么又能把‘说不出来的道’给说出来了呢?”(《老子究竟说什么》,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3、 道可以言说,但道非恒常而无变之道。 此种观点的特点是把“非常道”解释为“不是恒常而无变的道”,意即:道乃变化万端之道。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说:“道者,虚极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称。用可于物,故云可道。名生于用,故云可名。应用且无方,则非常于一道。物殊而名异,则非常于一名。是则强名曰道,而道无常名。”“用可于物”,即可应用于物。“非常于一道”,即不是常用一道而无变。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说:“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此处玄宗引《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来说明道之变化。 元代牛妙传说:“道者,……无适而不通,无可无不可,故云可道也。……盖道之为用,无乎不在,初无常定,故云非常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清代姚鼐说:“道,诚可道也。圣人之经纶大经、礼乐刑政,治天下之法,昔何尝不可道乎?然而非必常道之。时异势殊,道之所以用者,而后有不可施矣。”(《老子章义》) 当代朱谦之说:“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实则《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也。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也。自解《老》者偏于一面,以‘常’为不变不易之谓,可道可名则有变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则无变无易(林希逸),于是可言之道,为不可言矣;可名之名,为不可名矣。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老子校释》) 4、 道若可以践行,则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此种观点的特点是把“可道”之“道”解释为“实行”、“践行”,认为可践行之道,则非常道。 南宋李嘉谋(息斋道人)说:“常者,不变之谓也。物有变而道无变。……常之为道,不可行而至,……使其可行,即非常道。”(《道德真经》) 元代吴澄说:“道,犹路也。可道,可践行也。常,常久不变也。………若谓如道路之可践行,而道则非此常而不变之道也。”(《道德真经注》) 明代薛蕙说:“道本无为,若道而可为,乃有为之事,非常道矣。”(《老子集解》) 清顺治皇帝说:“上道字,制行之道。可道,行之也。常者,乃真常不变之道也。凡天下之道,可以制行者,非真常之道也。”(《御注道德经》) 近代张其淦(罗浮山豫道人)说:“凡事可践行者谓之道。然可道者,则非常道。”(《老子约》) 5、 道可以践行,但所行之道非常人之道。 明太祖朱元璋把“非常道”解释为“过常人所行之道”,即不是常人所行的道。他说:“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犹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无他欲,执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盖谓过人之大道。”(《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 当代吴林伯说:“老子之‘道’,为万物化生之总规律,或不易之定理。小、大由之,故曰‘可道’。《孟子•告子》:‘夫道若大路然。’《荀子•儒效》:‘道者,人之所道也。’‘道’既若路,人所共行,是‘道’字之义,与‘行’字同,曰论道之言‘甚易行’(七十章),行而宜之,故非寻常之‘道’。‘五千言’每言道而状之以大,岂非异常乎!”他将全句译为:“我的道,真像平坦的路,是可以通行的,也就不是寻常的道。”(《老子新解——〈道德经〉释义与串讲》,京华出版社1997年版) 6、道可以践行,所行之道中有非常之妙道。 南宋谢图南持此种解释。他说:“道本无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辟,可能共行如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谓此尔。可道者,犹可行也。可名者,犹曰可称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行,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欤!”(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其意为:道是可行的,但是百姓日行其道而不知其妙。不仅百姓不知,圣人亦不能尽道之妙。 7、道是什么道呢?不就是恒常之道吗? 当代徐梵澄先生持此种解释。他说:“帛书甲、乙两本,此句皆有‘也’字。‘也’为疑问语则同‘邪’,即‘耶’。——《礼记•曲礼》:‘奈何去社稷也?’《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也’皆同‘邪’。——第二字‘可’则‘何’之省文。——石鼓文‘其鱼维何’作‘其鱼维可’。云梦秦简‘购几可’即‘购几何’,‘可殹’即‘何也’。‘盗封啬夫可论’即‘盗封啬夫何论’。然则此第一句当作‘道,何道耶?’更进而问一句:‘非常道耶?’”“是谓非于恒常之道外别立一道。”(《老子臆解》) 8、道可以[被认识]由人们述说,[人们认识中的并加以述说的道]不是客观永恒的道。 此种观点见孙以楷、杨应芹所著《老子注译》(黄山书社1996年版)。 综上可见,老子短短的一句话,为诠释者提供了极大的诠释空间。这一状况的形成,当然与《道德经》原文过于简洁和具有模糊性有很大关系。 读者也许会问,以上这些不同理解,哪一种理解符合老子的原意呢?老子的原意真正可以搞清楚吗?按照当代哲学诠释学的观点,这样一种提问本身就是不合适的。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诠释者“筹划”的结果。他说:“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册,第3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伽达默尔指出,“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册,第380页。)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试图去弄清所谓作者的原意,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当代解构主义更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当我们阅读一句话的时候,它的意义由于某种原因始终是漂浮着的”。(转引自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第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因此,对文本做出的所有不同的诠释都是有效的和合法的,误读是不可能存在的。 按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观点,“诠释”就是“使用”,因为任何“诠释”都有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实用目的。这颇有点像中国古代所说的“六经注我”,旧瓶装新酒,诠释即创新。 当代另一些哲学家不赞成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激进主张。如意大利哲学家艾柯认为,文本确实给予读者大量自由的诠释空间,但这种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检验一种诠释是否过度的尺度就是“文本的连贯性整体”。他说:“对一个文本的某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不能,则应舍弃。”(艾柯:《过度诠释文本》,载《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第7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他还区分了对文本的“诠释”与“使用”。在他看来,读者对文本的“使用”可以是任意的,而“诠释”则应尊重文本本身的内在连贯性,因而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 笔者赞成艾柯的观点,“诠释”不能变成“使用”。 按照艾柯所提出的“文本的连贯性整体”的诠释尺度,将“常道”理解为“寻常之道”是没有依据的。考《道德经》中“常”字凡数十见,如“常无欲”、“道常无名”、“道常无为”、“复命曰常”、“常与善人”等,均作“恒常”解,无一例作“寻常”之。更为直接的证据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此句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乙本此句残缺,但有下句“恒名也”三个字。学术界认为,今本改“恒”为“常”乃是汉代人为避汉文帝刘恒之名所为。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三种,虽无此句,但“恒”字屡见,如“道恒无名”等等。此更可证“常”字原为“恒”字之有据。“常”与“恒”其义相同。恒,《说文》:“常也。”《广韵》:“久也。”常,《玉篇》:“恒也。”《正韵》:“久也。”可见,不管是写作“恒道”也好,还是写作“常道”也好,均是指永恒常在之道。因此,将“常道”解释为“常俗之道”(李荣)、“常人之道”(朱元璋)、“常人所谓的道”(司马光)、“寻常的道”(陈象古等)都没有根据。 但可道之“道”字的诠释无法从《道德经》本身找到内证,因为《道德经》全书其他各处之“道”字,无一作动词用者。因而释“道”为言说或释“道”为践行,“两行”可也。但在道是否可践行的问题上,亦可用内证证明第4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道德经》第41章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所行非大道乎?第53章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明确表达了行道的方法。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要人去效法道之“自然”而行。 除了文本的内证之外,必要的训诂学原则也是必须遵循的。解构主义所谓的“误读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语法阐释之上的。像世面上有本《道德经浅释》将“如享太牢”解释为“如坐大牢”,把“不自伐”的“伐“解释为“砍伐”,恐怕稍具古文常识的人都会发笑的。 另外,在诠释时,慎将文字作通假解。如俞樾解“非常道”说:“常与尚,古通,……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为上道。”(《老子平议》)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引用俞说。马叙伦则在《老子校诂》中论证俞说之非。他说:“本书后文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庄子•天下篇》言老子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者。’是则常者遮绝有无而为言,非上义也。”笔者按:今帛书本《老子》此句“常”作“恒”,可确证“常”非“上”义。 可见,诠释虽有自由度,但诠释的可能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限度来自于规则的遵守。如不遵守规则,则诠释完全变成了“使用”,因而也就失去了“诠释”的本来功能。像世面上有一本《道德经浅释》将“道可道非常道”解释成“道,可以叫做道,也可以不叫做道”,这是完全不遵守诠释规则,因而就超出了诠释的可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