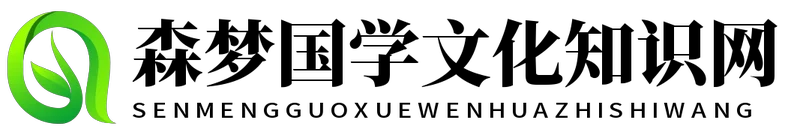摘 要:从“易道神”与“心理气”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重新刻画朱子学的宇宙论图景。理应当被理解为天地之心的德性,而气则是天地之心的发用,天地之心的功能在于通过主宰能力将理落实为气,由此以流行总体——也就是易体的形式展现自身。宇宙流行的无始无终与不间断性,并不意味着没有超越者,而是意味着作为超越者的天地之心无时无刻不在完整实现自身的德性。天地之心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心理气”模式不仅吸纳了“理气二分”模式,而且还有力地克服了理气二元割裂、理的实体化等问题,对四季循环也能提供更好的解释。而基于这一宇宙论模式,朱子学中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进行重新诠释。 关键词:朱子;易道神;心理气 心说是朱子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只注重从人心层面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朱子反复用来理解“心统性情”的“易道神”模式,在程颢的原始语境中乃是专就天道说,是具备独立的宇宙论意义的。也就是说,宇宙同人心的结构是一致的。“易道神”在人为“心性情”,在天为“心理气”。因此,对心说的讨论不应限于人心层面,而是应当扩展为一项专门的宇宙论研究,这正是本文的自我定位。本文将首先历时考察“易道神”的具体内涵,表明易体的基本含义是流行总体,易体同能够主宰理气的天地之心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澄清;继而通过辨析易体与天地之心的关系,重点讨论天地之心的超越性问题,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层面,而是理解天地之心的两个角度。从发用也就是“气”的角度来说,天地之心以流行总体的形式展现自身,所以固然有形而下的一面;但从天地之心的德性——也就是“理”的角度来说,天地之心有形而上的一面,“心理气”模式同将宇宙视为封闭自足的生命体的内在主义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据此,本文尤其强调,宇宙流行的无始无终与不间断性,并不意味着没有超越者,而是意味着作为超越者的天地之心无时无刻不在完整实现自身的德性。天地之心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最后本文指出,“心理气”克服了理气二分模式下存在的无法解释四季循环、理气二元、理的实体化等问题。 一、易道神 中国传统中的“天”的内涵十分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因此,历史上的思想家在理解“天”时,往往并不寻求单一的、明确的定义,而是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关联中对之进行整体把握。在北宋,程颢便从“易”“道”“神”三个角度理解“天”: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二程集》,第4页) 按朱子的理解,大程子这段论述的核心是《易》中的“终日乾乾”一语,也就是人道层面的工夫问题,但“易体、道理、神用”的论述本身却是专就天道上说,因而有独立的宇宙论意义。朱子的具体解释是: 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说起。虽是“无声无臭”,其阖辟变化之体,则谓之易。然所以能阖辟变化之理,则谓之道;其功用著见处,则谓之神;此皆就天上说。(黎靖德编,第2421页) 这是说“天”无形无影、无法捉摸,我们只能从“易”“道”“神”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把握它。首先,“易体”指的是流行变易的总体,是宇宙变化的全过程;其次,“道理”则是其中的本体,它是流行变化的所以然,隐匿于流行变化背后并且为其根据。如果关联于“神用”,那么“道理”就表现为流行变化不失其秩序条理。而“易体”之所以具备功用,也正是因为它蕴含着“道理”。正如钟表之所以能计时,是因为蕴含着计时的原理;最后,“神用”具体指阴阳的屈伸往来、造化之迹、各种感官可以把握的表象。它是“易体”之功用的展现,也是“道理”的落实。 这种解读还比较简略,仍然保留着一定的解释空间。“易道神”其实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方式,而朱子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他很早便将心体与易体关联。但这种关联一开始着眼的仅仅是心体流行不断的特点,将它比拟于易体的流行变化,并未涉及心体的主宰问题。而随着讨论的深入,朱子则越来越倾向于完全从心体的结构理解易体,强调宇宙与人心的同构性,将人心视为一个变化流行的小宇宙。 《朱子语类》载: “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理则谓之道”,在人则性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所谓易者,变化错综,如阴阳昼夜,雷风水火,反复流转,纵横经纬而不已也。人心则语默动静,变化不测者是也。体,是形体也,(贺孙录云:“体,非‘体、用’之谓。”)言体,则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则形而上者也。故程子曰“《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亦是意也。(同上,第2422页) 问:“昨日先生说:‘程子谓:“其体则谓之易。”体,犹形体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说个阴阳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尝曰:‘在人言之,则其体谓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个动静感应而已。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几个字,便见得。”(同上,第1614页) 这两条语录观点大致相同。在此,朱子明确将易体对应于心体,但他着眼的并不是心体的主宰能力,而是它流行不断的特点。朱子旨在用心体的语默动静,比拟易体的阴阳流转,易体的基本内涵是流行变化的总体。他并没有否定宇宙存在主宰,但至少在这两条语录中,主宰问题并没有进入讨论的范围。此外,朱子还明确指出易体属形而下,那么易体同神用便是重叠的,二者都可以归并为气。“易道神”实际上仍然是理气二分、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分的模式,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上述两段材料的第一条为程端蒙、叶贺孙所录,可以确定时间为绍熙二年(1191年),朱子62岁。第二条为辅广所录,在朱子65-71岁间。翟奎凤进而推测,以易体为形而下的观点,可能主要见于朱子62-65岁之间。(参见翟奎凤,2021年,第74页) 在后来的讨论中,朱子明确否定了上述观点,代之以“易该体用”: 黄敬之有书,先生示人杰。人杰云:“其说名义处,或中或否。盖彼未有实功,说得不济事。”曰:“也须要理会。若实下工夫,亦须先理会名义,都要着落。彼谓‘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其说有病。如伊川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方说得的当。然伊川所谓‘体’字,与‘实’字相似,乃是该体、用而言。如阴阳动静之类,毕竟是阴为体,阳为用,静而动,动而静,是所以为易之体也。”人杰云:“向见先生云,体是形体,却是着形气说,不如说该体、用者为备耳。”曰:“若作形气说,然却只说得一边。惟说作该体、用,乃为全备,却统得下面‘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两句。”(黎靖德编,第2890页) 此条为万人杰所录,考虑到其中有对此前观点的明确否定,那么时间应当至少在朱子65岁之后。这段材料意涵丰富,要点有四:首先,朱子还是从阴阳动静变化来理解易体,易体的基本内涵依旧是流行总体。这是对前述观点的继承。其次,由于阴阳都属气,故而朱子所谓的“阴为体,阳为用”,并不意味着阴和阳是体用关系。他曾指出:“未发之前,太极之静而阴也。已发之后,太极之动而阳也。”(见郭齐、尹波,第1969页)“未发者太极之静,已发者太极之动也。”(同上,第2345页)在论人心时,朱子曾引程子之言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黎靖德编,第1512页)据此,阴静为体指的是易体流行的寂然不动状态,此时易体浑然是本体之体段,本体通过易体呈露而尚未落实为功用。这与人心未发时为中、中所以状性之体段是一致的。而阳动为用指的是易体流行的感而遂通状态,此时功用已形而本体寓于其中。因此,阴体阳用真正的理论意义,是区分出易体流行的未发与已发两种状态,并且相应地分出易之本体与易之发用。第三,易之本体即道理,易之发用即神用,这便是“易该体用”。朱子所谓的“却统得下面两句”,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的。最后,联系前引朱子关于太极的论述,我们可以说易之本体是太极,易之发用是阴阳流行。所以“易该体用”“易该道神”也可以理解为“易该理气”。易体固然仍保留了形气的一面,但已不能再单纯地归为形而下,而是包括体用,也就是兼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一体流行。这样理解的话,“易道神”不仅区别于理气,甚至还容纳了理气结构。同时,“易道神”与“心性情”也基本吻合了。 在另外的一些讨论中,朱子还论及了易体流行中的主宰问题: 正淳问:“‘其体则谓之易’,只屈伸往来之义是否?”曰:“义则不是。只阴阳屈伸,便是形体。”又问:“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发用便是情。”(黎靖德编,第2423页) 先生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犹心也;道,犹性也;神,犹情也。”翌日再问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摄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为春夏,所以为秋冬之理是也;至发育万物者,即其情也。”(同上) 以上两条语录皆黄所录,在朱子59岁时。在此,易体的基本内涵同样是流行总体,是阴阳屈伸往来、四季循环变化的总过程。朱子之所以用心体比拟易体,着眼的也是这一点,这和前述讨论是一致的。不过,问者却提出了进一步疑问:在流行的意义上,我们固然可以说易体与人心有相似性,但是人心具备的主宰能力,易体到底有没有?对此,朱子似乎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而讨论天地之心的问题。他指出,万物发育是天地之情,其根据是天地之性。显然,二者指的分别是气和理。至于天地之心的作用,则是主宰理、气。朱子意在指明,无论是人还是宇宙,都有心在其中发挥主宰的功能。人心层面的“心性情”,对应于宇宙层面的“心理气”。而如前所述,既然理与气可以分别等同于道理与神用,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天地之心和易体是不是一回事?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理解“心理气”的内涵。 二、心理气 认为人心层面的“心性情”对应于宇宙层面的“心理气”,这看起来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说法。毕竟在惯常的理解中,理气二分才是我们熟悉的朱子学的宇宙论模式。但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这一判断。在过往研究中,我们往往习惯于理气二分的思维模式,对朱子学中的诸多范畴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元处理。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心统性情”的问题,如钱穆、刘述先、李明辉等学者都认为,既然朱子学中的心不属理,那便应当属气,是形而下的。针对这些观点,陈来指出,理气二分的模式只适用于存在实体,它将事物分解为形式、质料两个要素,不能直接挪用到对心的理解上。(参见陈来,2010年a,第127-128页)而朱子在理解“心统性情”时,使用的其实是易道神模式,它将心理解为一个变化的功能系统,并相应地分出系统总体、运行原理、系统作用三个要素。(参见陈来,2010年b,第294页) 更进一步,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易道神”本身是专就天道上说,因而有独立的宇宙论意义。它首先是宇宙的结构,其次才被用来理解人心。天与人是一致的,易道神在人心为“心性情”,在天道则为“心理气”,这也正是前引黄所录语录中朱子要表达的意思。而更重要的是,“心理气”同“理气二分”并不是冲突的,它完全可以容纳理气模式,并且能更好地解决理气模式存在的问题,这一点本文稍后还要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那么,如何理解“心理气”的具体内涵?唐文明认为,天地之心的主宰作用关联于理表现为理的能动性,关联于气则表现为气的灵敏性。(参见唐文明,第160-161页)也就是说,如果离开天地之心的主宰作用,那么一方面理的规定性便无法落实,因为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另一方面气也就成为僵死的质料,不存在妙用、神用。因此,宇宙流行是心、理、气三个因素互相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这一架构早在《仁说》中便已有了成熟的表达: 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见郭齐、尹波,第3328页) 《元亨利贞说》则谓: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同上,第3302页) 这两段话意义明确,架构清晰。朱子以天地之心对应人心,元亨利贞对应仁义礼智,春夏秋冬对应爱恭宜别。因此,理即天地之性,气即天地之情。而本文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按照这一架构,“理”的首要内涵绝非流行变化的规律法则——虽然它并不排斥这一层意义——而是天地之心的德性。“气”也不是单纯的质料材料,而是天地之心的功用。理是气的根据,气是理的落实。天地之心则依靠其主宰能力,将自身的理实现为气的运行变化,例如,将自身的元德落实为春气生物,由此才形成宇宙的流行。而在宇宙流行之后,天地之心仍然依据理来主宰气,故而气才呈现出循环有序的特点。按照这种架构,就理内在于天地之心而言,可以说理是天地之心的本性;就宇宙的流行是为了实现理而言,理是宇宙流行的目的;就造化流行没有间断,天地之心不受遮蔽而时时刻刻将理落实为气而言,天地之心是一个完满的、充分实现本性的无限者。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再来考虑天地之心与易体的关系。如前所述,无论是理还是气,都内在于天地之心。气的流行运转,本质上是天地之心在发挥自身的功用、实现自身的德性。所以“主宰理气”的直接表现就是“流行总体”。在此意义上,天地之心就是易体。而根据此前的论述,从“易该体用”“易该理气”“易体有未发、已发时”“理为易之本体”“气为易之发用”这些特点来看,易体的结构显然与心体完全吻合,这也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事实上,单单是朱子屡屡将易体与天地之心相对应这一点,便足以说明天地之心就是易体。二者只是名义侧重不同,后者重在流行变易的总体,而前者重在对理与气的主宰义。 但我们仍不得不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如何理解天理的形而上地位?如果说心、理、气都属“形而下”,那么当我们说天地之心是易体时,实则是说天地之心就是宇宙整体、万物总体。按这种思路,宇宙就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生命体,不存在宇宙之外的超越者。它有自身的本性与目的(理),同时也有实现本性的深微倾向(主宰),而其运行(气)则是在不断地实现自身的本性。就其处于不断的流行变易而言,我们称之为易体;就其有明确的主宰与目的而言,我们称之为天地之心。而如果说天理是形而上的,那就相当于说理既外在于宇宙,又内在于宇宙,这如何可能?并且,进一步的问题是,天地之心是不是形而上的?如果是,那它和易体的关系又将变得模糊不清,毕竟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流行总体”属于形而上;如果不是,那么天地之心如何能对形而上的天理有主宰作用? 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我们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理解。当我们作出这一区分时,其实往往是以宇宙为基准,认为宇宙内为形而下,宇宙外为形而上。这样一来,二者就成了非此即彼的两个维度。如果天地之心是形而下的,那么它是宇宙自身的一种主宰力量、实现本性的倾向;如果天地之心是形而上的,那么它是宇宙之外的超越者。这两种观点是无法协调的。但是,在朱子那里,形而上与形而下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最典型的便是对“人心”的定位: 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补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问:“如此,则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黎靖德编,第87页) 我们看到,朱子始终拒绝对心体属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作出判定。而如果人心与天地之心的结构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可以说,天地之心并不能被判定为单纯的形而上或形而下。事实上,朱子的思路可能并不是以宇宙为基准划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再以此来判定天地之心的归属。恰恰相反,形而上与形而下,更多地是理解天地之心的两个不同视角。从“气”的角度来说,天地之心必然实现自身的德性,也就必然以宇宙流行的方式展现自身。在此意义上,天地之心有形而下的一面,它内在化于宇宙万物中;但从“理”的角度来说,理的形而上地位说明了天地之心超越的一面。天地之心可以不发挥自身的德性,由此宇宙统体将归于虚无。而即便如此,天地之心仍然可以通过理而演绎出新的宇宙流行。正是在此意义上,朱子才会说:“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同上,第4页)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超越于宇宙万物之上的形而上的一面。 按这种模式,我们仍然可以说天地之心是易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地之心等同于流行总体、宇宙整体,因而并不是超越的,而是意味着作为超越者的天地之心的完满性——必然实现自身的德性,决定了它只以流行总体的形式展现自身,也就是必然通过生物而内在化于宇宙中。天地之心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面性,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 三、反思理气二分模式 根据目前的分析,“易道神”-“心理气”同“理气二分”其实并非对立的两种模式。前者不仅吸纳了后者,并且有力地克服了后者存在的各种问题。陈来已指出:“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乎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突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陈来,2014年,第46页)所谓的仁体,也就是天地之心、易体、道体。这就表明,我们有必要基于“易道神”与“心理气”模式对理气二分的模式进一步反思。在此,我们主要指出以下两点: 首先是关于如何处理四季循环的问题。如前所述,朱子“易该体用”的理论意义之一,便是区分出易体也即天地之心的未发、已发两种状态。这在解释四季循环的问题上是有其优势的,《朱子语类》载: 伊川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盖谓天地以生生为德,自“元亨利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静而复,乃未发之体;动而通焉,则已发之用。一阳来复,其始生甚微,固若静矣。然其实动之机,其势日长,而万物莫不资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发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而可见也。若其静而未发,则此之心体虽无所不在,然却有未发见处。此程子所以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亦举用以该其体尔。(黎靖德编,第1791-1792页) 这里重点要讨论的是“冬至”的问题。如前所述,天地之心是无时无刻不在完整实现自身德性的完满者,这就表现在其不停歇的生物功用上,表现为造化流行没有间断。正如朱子指出的:“天地生物之心,未尝须臾停。”(黎靖德编,第1791页)可问题是,冬至日呈现的却是极端的万物凋零、肃杀消亡,而黑夜也到达了最长状态。那么,如何理解此时的天地生物之心?事实上,在世界其他文明的经验中,漫长的黑夜、肃杀的冬至往往被体验为宇宙生命力的枯竭,与此相伴的则是沉重的焦虑。也就是说,造化流行被体验为有间断、有停歇的。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各种复活仪式便被发明出来。这些仪式旨在回到宇宙初生的原点,重新恢复其生育万物的活力。而对朱子而言,他必须解释为什么万物消亡了,天地之心却没有间断。就卦象而言,便是如何理解复卦中的一阳来复。 在上引语录中,朱子指出天地之心“静而复,乃未发之体;动而通焉,则已发之用”。静而复的“未发”意味着天地之心的发用逐渐收敛,万物逐渐凋零。天地之心越来越明晰地呈现为天理之体段;动而通的“已发”意味着天地之心的发用逐渐显著,万物逐渐生长,此时本体寓于其中。按这种理解,冬至之时无物可见,天地之心处于完全寂然不动的收敛状态。而也正是此时,天地之心随即便又趋向已发,万物开始复苏。正如黑夜一旦达到最长,便马上开始缩短。这一过程只有动静、阴阳的转换,而没有造化流行的间断。一阳初生的复卦卦象正说明了这一点。按这种理解,冬至实则潜藏着向万物生长转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天地之心的断裂:“到冬时,疑若树无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敛在下,每实各具生理,更见生生不穷之意。”(同上,第1729页)朱子同时强调,天地之心只有回到这种收敛状态,才能有进一步的发用: 下梢若无这归宿处,便也无这元了。惟有这归宿处,元又从此起。元了又贞,贞了又元,万古只如此,循环无穷,所谓“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说已尽了。(同上,第1513页) 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见郭齐、尹波,第2864页) 事实上,无论是万物生长还是万物消亡,严格来说都只是流行表象。隐匿于其背后的,则是天地之心的翕聚与发散、静与动的循环,以及元亨利贞、仁义礼智四德的更相为用。因此,冬至时万物消亡的实质,并不是天地之心自身的断绝,而是处于元贞交际、仁智交际的天地之心展现自身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天地之心循环不已中的一个环节。只有着眼于本体层面的天地之心的四德运转,而非表象层面的万物肃杀,我们才可以说造化流行没有间断。 正是因为天地之心以易体的形式展现自身,所以可以广泛地用以处理关于流行、循环的动态问题。相比之下,按陈来的分析,理气二分模式则主要适用于存在实体的要素分析,分别对应于形式与质料;此外,还适用于活动的根榞性分析。(参见陈来,2010年a,第127-128页)这两类分析可以说都是静态分析,那么当面对造化流行的不同阶段、循环、发散、收敛这些动态的问题时,理气二分的模式就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易体、天地之心的概念。因此,表面上看,“心理气”同“理气二分”仅仅是概念使用上的不同。但实际上,二者的差异更涉及了思维结构、思维方法,乃至于对本体的认识。理气二分模式之所以重在静态分析,根本上是因为理、气虽然也存在不离的关系,但仍然可以孤立地考察每个要素。也正因如此,在现有的理学研究中,朱子哲学屡屡被判为二元论,作为本体的天理也时时遭受实体化的批评。而在心理气模式中,心、理、气三个因素互相定义。每个要素的内涵与意义,都是在同另外两个要素的相互关联中显示出来的。朱子屡次强调观察名义要活看、要各有地头说,也正是在强调这一点。正如李煌明指出的,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是“朱子哲学核心的思维结构,是其总纲与枢要,是对待与流行的圆融”。(参见李煌明,第56页)因此,这三个要素似分实合、圆融无碍,共同构成了对宇宙一体流行的阐释。这样,本体就显现于流行发用中,同时又不消解自身的独立性。 由此,我们可以进而探讨第二个问题:心理气模式如何有效地避免理的实体化问题。我们知道,程朱一系理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理与气的严格区分。尽管朱子同时也强调理并非有形的实体,强调体用一源,但他的许多说法仍然不免有将理实体化的倾向。例如,他说:“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黎靖德编,第3页)“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同上,第64页)又谓:“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同上,第3页)“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同上,第65页)诸如“挂搭”“顿放”“附着”的说法,仍不免使人对天理产生“如有物焉”的印象。正因如此,元明以后才会开启气学转向,这在学界的已有研究中往往也被刻画为对理的“去实体化”(参见陈来,2003年,第1-17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罗钦顺的论述: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罗钦顺,第89页) 这一论述的核心在于认为天地之间只有气的运动变化,而所谓的理只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规律、法则,这就在宇宙论上走向了气的一元论。罗钦顺以降至于王廷相、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的气学,以及程瑶田、凌廷堪等人的礼学,乃至于后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可以说都同这一气学转向有密切的联系。其共同特点是在宇宙论层面寓理于气,在人性论层面逐渐离开性善论传统,转而对经验性的多有肯定,在历史层面则强调历史自身的大势规律,而非用高于历史的价值去规范它。一言以蔽之,即消解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严格区分。 本文无意于评判这种模式与程朱孰优孰劣,但意在指出,心理气的模式可以较好地克服理气二元、理的实体化问题。就前者而言,按照心理气模式,理与气被统一在天地之心上。理是天地之心的德性、品质,是宇宙流行的根据;气也不是与理脱离的质料,而是理的实现。这样,聚焦于天地之心,理与气就构成了体用关系。理与气的结合问题,被理解为天地之心依靠其主宰能力,将自身的德性(理)实现为发用(气),由此呈现为易体流行的过程。就后者而言,理的形而上地位并不意味着它是独立的实体,而是意味着天地之心的德性(理)先于其功用(气),并且构成其根据。天地之心可以不实现自身的德性,那么宇宙将归于虚无;而天地之心仍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德性重新展开宇宙的流行。就理的形而上而言,天地之心是一个超越者;就气的形而下而言,这个超越者必然且只以宇宙流行的面貌展现自身。是故可以说,天地之心是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这一方面严格保留了二者的区分,另一方面又将二者统一起来。反过来说,无论是消解超越、只讲内在,还是割裂超越与内在的统一关系,都是不符合朱子本意的。 四、结 语 正如本文分析的那样,宇宙层面的“心理气”架构其实早在《仁说》《元亨利贞说》等文献中便已有成熟的表达。并且,考虑到天人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易道神”与“心性情”的对应关系,有理由认为“心理气”比“理气二分”更符合朱子学的内在逻辑。这并不是说理不再是朱子学的首要概念,而是说理的形而上地位、普遍性等特点只有在“易道神”“心理气”构成的功能系统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心、理、气是相互界定、不可的三个概念。并且,立足于“心理气”模式,我们还可以对朱子学中的不少问题进行新的理解。例如,以往我们常常认为朱子的“主敬”只有心理学意义而无伦理学意义,其功能仅限于意识的控制与集中,因而是“缺少头脑”的。(参见吴震,第160-161页)但事实上,朱子《敬斋箴》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见郭齐、尹波,第4039页)主敬的意义不仅包括、甚至还不限于伦理学,它本质上是一个与超越者沟通的方式。而这只有在人心与天地之心的对应关系中才有可能。又如关于格物致知,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知性取向的工夫。但按照“心理气”与“心性情”的存在论结构,天地之心完整无遗地发挥了自身的能力(理),而人与万物则受限于形质而处于有限性中。因此,格物致知应当被理解为人在不断与物交接中突破自身的局限性,不断向天地之心之德靠拢的工夫。这里不存在道德与知识的区分,而只有天与人的沟通。此外,也只有以天地之心的全体大用为基础,我们才能明白朱子将人心视为万事之本的理解并不是一种贫乏的说教。人心的所有功能,都是天地之心功用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工夫的目的,正是使人心能够全面充分地展现自身的这些功能。 参考文献 [1] 陈来,2003年:《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载《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 2010年a:《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b:《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二程集》,2004年,中华书局。 [3]郭齐、尹波,2019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4]黎靖德编,2020年:《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5]李煌明,2017年:《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哲学的思维结构与理论纲脉》,载《哲学研究》第4期。 [6]李健芸,2021年:《朱子“复见天地之心”阐释中的未发已发问题——兼论“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载《哲学动态》第5期。 [7]李明辉,1993年:《朱子论恶之根源》,载钟彩钧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中国“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8]刘昊,2023年:《道兼理气:朱子学理气论的经典诠释背景及其影响》,载《哲学研究》第7期。 [9]刘述先,2015年:《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罗钦顺,2013年:《困知记》,中华书局。 [11]钱穆,2011年:《朱子新学案》第2册,九州出版社。 [12]唐文明,2019年:《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13]吴震,2018年:《朱子思想再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4]翟奎凤,2021年:《“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载《中国哲学史》第2期。 2022年:《坤复说辨:朱子论未发时心之知觉》,载《哲学研究》第8期。 作者:黄永其,1995年生,浙江温州人,清华大学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礼学。